地方模式:探索中国道路
摘要:胡温政府执掌中国初年,全国人均GDP迈过了1000美元的大坎,进入学界公认的社会转型期。然而,“中国转型”未艾,“中国模式”却兴起了。
胡温政府执掌中国初年,全国人均GDP迈过了1000美元的大坎,进入学界公认的社会转型期。然而,“中国转型”未艾,“中国模式”却兴起了。
自2004年开始,“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媒体上的一个关键词,尤其是2008年之后,伴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以及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相对稳定的表现和争得GPD世界第二的宝座,中国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期,“中国模式”被鼓噪一时。
然而,不管“中国模式”是否存在,都必须承认,中国尚未找到稳定的、形成社会共识的经济发展途径,政治体制改革仍被各阶层倡导,中国道路还在探索阶段。而这种探索就存在于地方治理实践之中,其中广东模式、重庆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最具代表性,区域性的竞争正在加速中国地方治理特点的形成,而它们将为未来的中国模式提供有益经验。
在一个单一体制、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国中,一竿子到底的统一政令极有可能造成一种僵化而又蕴藏极大风险的社会局面。虽然现在中央的宏观政策依然是解读中国的重中之重,但理解中国的区域性的行为模式和制度倾向,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中国并不存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小岗村这样成功的制度变革并非常规现象。如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所言,“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现在,我们的改革历来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就是革命了。当然我们改革过程中,允许某些地方先行先试,进行试点,这些都是在中央许可下进行的,中央有这个意图。”
广东模式--社会管理创新
思想解放让广东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前沿地带。过去几年,广东最为引人注目的改革是汪洋领导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而这其中又以顺德为改革“尖兵”。
顺德在2009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就已“石破天惊”,它创造性地使用“党政联动”模式精简党政机构,被广东省政府作为推进大部制改革的一次大手笔在全省推广,当时的改革核心在于行政管理机制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职能。
2011年开启的社会管理创新改革更具野心:以社会体制综合改革统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三大改革,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德模式,解决社会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腿短”的问题。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法定机构的试点、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等内容都引人瞩目。顺德设计了明确的权力架构:区委区政府负责重大决策和综合性政策的制定,区属部门负责专业性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实施,区法定机构、事业单位和镇街负责执行,同时也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服务。
虽然仍然处于政府威权体制的领导之下,民间结社自由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文化类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很明显,广东正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公民社会的发展。
广东的社会管理创新改革最关键之处在于放权,这对于一向以集权为基本政治逻辑的中国政府机构来说等于是“对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但这是在面对改革停滞的巨大风险时不得不为之事。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肖滨指出,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渡中的一个形态。
当然,广东的改革也具有所有地方政府都难以克服的困境。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断批评国家部委利益法制化,对广东改革形成阻碍。正是这种体制化障碍,让很多人对广东的改革成败持保留意见。
重庆模式--领导人意志
曾经甚嚣尘上的重庆模式先于广东模式提出,也先于广东模式走向没落。但是不可忽视它在后发地区的话语竞争优势。
“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薄熙来的话语充满着感召力,意思就是先公平地分蛋糕,再快速地做蛋糕,对老百姓来说,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正是薄在重庆的施政理念。
2010年,重庆市的GDP增长率达到17.1%,排名全国第二,2011年又以16.4%的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无法确认重庆的高增长是否是“分蛋糕”所产生的积极性带来的,但重庆市民高昂的热情似乎不假。
重庆是市场主导力量较弱的地区,政府的强力主导具有先天优势,薄熙来正是以“土地为资源,金融为杠杆”的赶超型方法快速推动经济。同时大力鼓吹“共同富裕”,大造廉租房。
经济学家杨帆将重庆模式概括为:一次在中国转型期突然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采用激进手段在局部地区大幅度改变利益格局,甚至违背法治理念,大规模杀富济贫。这在一定时期有效,但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恐慌也是必然的,所以在内部失控的突发事件中迅速失败。
在外界眼中,薄熙来主导下的重庆,具有毛时代的极左色彩,最突出莫过于以运动的方式大搞“唱红打黑”。而在这背后,是对民主和法治的无视,领导人意志覆盖了整个党政官僚体系的一般制度性倾向。“李庄案”得到的超乎想象的关注也能表明外界对所谓的“重庆模式”危险性的警惕。
苏南模式--政府公司化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地方政府公司化”为特征的苏南模式是改革开放数十年发展积累的结果。
改革开放之初,江苏地方政府从中央获得了财政、外汇和外贸的部分自主权,地方政府有了追求收益的明确利益动机,就参照国家资本主导工业化的管理方式来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苏南地区以地方政府来全额占有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降低了地方工业化启动成本,快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乡村两级行政机构都以总公司名义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之下,苏南经济实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增长。
1998年之后,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模糊的产权成了企业发展的阻碍,大规模的改制由此展开。
经过数轮产权制度改革,苏南模式演变为如今的新苏南模式,但政府主导始终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其特点集中体现在经营城市、培育大工业区、实现聚集发展。在中国的“招商引资”热潮中,这种模式正在逐步地复制到全国。
与新加坡合作诞生的苏州工业园区当属苏南模式的代表之作。这里有大量高端企业进驻,已然成为苏州经济的增长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正鲜明地体现了苏南园区经济的政府主导特点。
苏南模式的隐患也不可忽视。在发展园区经济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并不容易,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很可能将在这种模式中进一步拉大。若资本与地方政府联合,强行推动土地资本化,恐怕会引发巨大反弹。2010年围绕着拆迁产生的通安群体性事件就是代表。
浙江模式--民间力量
不同于苏南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温州私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模式也曾被看成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希望之星。
在这片区域,基层政权势力不强,而家族纽带却十分牢固。温州人用企业家的智慧,不依靠任何权力,崛起于草根,创造了令人炫目的财富。他们不依靠政府投资或者外资引进,而运用民间资本、国内外市场需求撬动经济车轮。温州政府也顺应这种形势,“无为而治”,间接确保了民营经济的繁荣。
以温州为标本,我们能看到浙江的整体性展现:县域发展模式--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核心产业,每个县都不是一两家大企业说了算。这种多中心秩序的经济结构基础,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温州现有市级行业协会80多家,其他地区的温州商会超过200家,形成了温州的行业自治机制,这种市民社会的发育也正是广东目前的改革所追求的。
不过温州经济也有自己的问题:散而乱,本地企业始终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链规模优势难以形成;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产业发展,公共品短缺;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于经济组织发展,社会自我组织能力薄弱等。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急需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是温州数千亿元的民间资本像“幽灵”般在全国游荡,形成温州“炒房团”。近两年的民间借贷泛滥、少数民营企业主“跑路”正是这些问题的表象。
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但由于缺乏明确而坚定的中央性授权,温州的金融改革进入一种尴尬的状态,改革本来应有的发展民间正规银行、利率市场化等环节,几乎没有进展。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突破了自身瓶颈,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还要看温州人的自主创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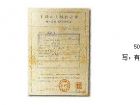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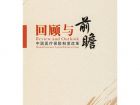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