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和莫斯科之行
摘要:1988年10月,中国社科院农村所选派我和蔡P同志一起出访波兰、苏联,原订计划访问华沙、莫斯科四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去一个我从童年时代就梦想过的地方,也是令我们这代人十分神往的国家。我的兴奋和激动是很自然的,虽然那时我已进入老年。
1988年10月,中国社科院农村所选派我和蔡P同志一起出访波兰、苏联,原订计划访问华沙、莫斯科四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去一个我从童年时代就梦想过的地方,也是令我们这代人十分神往的国家。我的兴奋和激动是很自然的,虽然那时我已进入老年。
10月21日晚10点,我们乘中国民航国际班机从北京机场起飞,8小时后飞机在加沙加油,第二天下午2点抵达法兰克福,约5点钟到达波兰首都华沙。
由于语言障碍,波兰科学院的同志在机场没有接到我们。他们用英语和波语通过广播呼我们,而我和蔡P只懂俄语。幸好,同机有一位叫米克的波兰朋友,约我们跟他一起先去他的家。这位米克先生曾到过上海,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们在他家吃了菜点后就去了中国使馆。很奇怪,中国使馆的人对我们并不热心。最后我们只好跟一位叫成章的中国进修生一起入住华沙大学。
第二天上午,在华沙大学我见到了波籍华人胡佩芳女士。胡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嫁给了一位人民大学的波兰留学生,后移居波兰。中国改革开放后,胡佩芳回过中国,对来波兰访问的中国人士十分友好。她得知我是人民大学的老校友,就格外热情,立即陪我们去留学生活动中心。这留学生活动中心是专门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服务机构,只提供住处和简单炊具,每人每日收费5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费标准了。胡佩芳最后决定约我们住到她家里。她的家虽然房子不大,但很方便,还能吃到中国饭菜。正巧,那几天她一个人在家,又没有别的事,可以陪我们。由于有胡佩芳的关照和陪伴,我们在华沙的活动一切顺利,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乡亲”的温暖。
10月24日,胡佩芳陪我们去使馆,经一秘袁先生同波兰科学院联系,中午会见了波兰科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所所长米修纳教授。波方付给我们每人生活费10,000提纳尔。10月25日由胡陪同跟农村所的同行会谈,中午一起吃饭,饭后去米修纳教授家。
同波兰农村所同行的会谈,主要是了解波兰农业与的情况以及波兰农业经济管理改革的情况。波兰全国下设29个省,有7万多个乡镇,乡村人口85000人,约2万农户。当时的农经改革主要是改革计划价格管理体制,改变过去由国家垄断定价的办法。波兰有农民党,1980年后,在团结工会中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在波兰,农产品价格的决定,农民党同统一社会党一样具有否决权。1980年后, 波兰有各种社会监督机构并办有一个专门刊物——《否决》。波兰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波兰科学院,主要研究理论问题,另外还有高校和政府各部的研究所,主要研究实际问题。
波兰农业与农村研究所共有70余人,60名为研究人员,10名为行政工作人员。最大的研究室是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室,共30人。农村社会学研究室20人。另有一个信息数据处理统计资料室,10人左右。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研究刊物、对外交流和经费来源及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此后,在波兰几天的活动也很简单:
10月25日至26日同米修纳交流。
10月27日参观访问波兰农户。
10月28日参观华沙河及美人鱼。中午商谈第二年他们来中国交流的问题。
10月29日去中心购物,下午参观教堂、古城、夏宫。
10月31日逛自选市场,乘公车自由活动。下午16点半离华沙赴莫斯科。
在波兰短暂的10天里,学术交流活动简单而平谈,但波兰悠久历史文化的印象却是令人难忘的。在古城、夏宫、教堂、华沙河、肖邦音乐广场,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欧洲文明的特别气息。它是那样的浓郁,那样的古老而别致,使接触到它的人不能不为之倾倒,难以忘却。
一种文化土壤培育着一种人文情感。在波兰、在华沙,几乎随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二战影响,虽然那场战争已过去近40年了。在街道上,可以见到各种战争纪念物,有的墙壁上常年点燃烛火,悼念牺牲在那里的受难者。
波兰人很讲文明礼貌,对中国人特别友好。他们对我说,即使语言不通,只凭微笑也能传递友谊。最使我感动的是在一辆返回住处的公车上,我忘记了下车,车已开过站很远了,司机竟专门为我停车,让我下车,不仅不大声吼叫责怪,还连声向我道歉。这是我从来未经历过的。
波兰的文化传统也充分体现在这个民族的各种工艺品上。在参观游览点,人们可以很便宜地买到各种精致的小古董小玩意儿,如铜制的华沙美人鱼、木质的精美挂盘等。那时在我们中国这类小东西奇缺。我特别喜欢这类小东西,每见到那些玩意儿就爱不释手,尽自己的购买能力购买。他们发给我的生活费,除了吃饭就全花在这些小玩意儿上了。直到现在,我的床头墙上仍然挂着从波兰带回来的这类小玩意。它们随时勾起我美好的回忆。
在华沙,我花15000提纳尔买了一件黑白花呢短大衣。胡佩芳说我买的那大衣是时装,太贵了。我当时并不懂什么是时装,只是用尽手里的钱买了自己喜欢的一件东西。至今已十几年了,我每年冬天都穿那件大衣。它依然不显旧,也不过时,不仅我喜欢穿它,还受到青年们好评,可见它真是一件高质量的东西。
在华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我们住地附近的那个美丽的公园。那园中央有一座由6条向天斜立的黑色石柱组成的二战英雄纪念碑。石柱中间是一尊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卫国战士铜像。那庄严的纪念碑散发着英雄气慨,它把每个走近它的人带到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早上,我喜欢在这园中散步,远处一只可爱的小白狗也跟人一样不慌不忙不声不响地低着头走在秋叶飘落的地上。那披满落叶的英雄纪念碑永远屹立在我心中,那是成千上万二战英雄的血肉与心灵的像征啊!
11月1日是波兰的“亡人节”。10月31日下午当我们离开华沙时,街上已经到处点燃了星星点点的烛火,它像征着这座英雄城市不屈的记性和灵性。
10月31日下午6点钟左右我们飞抵莫斯科。接待我们的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他们安排我们住在莫斯科十月大街苏联科学院旅馆,我的房间号是1307,陪我们的翻译是科学院一位叫安德烈的青年研究人员。
在莫斯科,从第一天起我就充分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雄伟和壮丽,但她远不是我年轻时梦想的、歌中唱的那样美丽,特别是满城烟筒林立,很容易使人产生煞风景之感,但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像征,谁能怀疑它的合理性、正确性!
莫斯科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特别是红场上的列宁墓、无名烈士纪念碑和日夜燃烧的长明火。她辐射出的庄严神圣气氛,令人激动,感人肺腑。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苏联的国庆日。那天,红场上挤满了各地涌来的人群。他们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这正是我们过去在舞台上电影里见到过的俄罗斯舞表演者的打扮。站在红场周围维持秩序的是年轻的红军战士。这画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那天,我在日记中不胜感慨地写到:“苏联的今天真是我们的昨天啊!”
在莫斯科,我们访问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和《农村生活报》主编,参观了工厂和农庄,听了他们关于苏联农村改革情况的介绍。他们说,苏联几代农民都不会种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杀死了许多富农,农民都成了农庄的雇工。那些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变革,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听到这些,作为一个革命的追随者,我的感情是矛盾的、沉重的,但面对这一切,我不能不以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事实。革命者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原则不就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吗?而真理深埋在事实之中,服从真理就必须承认事实啊!真想不到,消灭富农的直接后果竟导致这样的悲剧。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中,苏联农民不愿承租农庄的土地,这和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苏联同志们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是成功的。
10月4日安德烈陪我们参观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下午我们一起吃饭,那鱼子酱和红菜汤的味道的确比北京莫斯科餐厅的更地道、更鲜美。
在莫斯科的实际收获是在“儿童世界”买到了不少的儿童玩具和用品,主要是各种冰鞋和小工艺品。那些苏联冰鞋价格便宜,质量又好。冰鞋的价格30卢布一双,铸在冰刀上,这表明价格是固定不变的。那些价廉物美的文体用品,对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商品短缺的中国人很有吸引力。我贪婪地给家里每个孩子买了一双冰鞋,还专门为小萌买了打冰球的冰杆,为苗苗买了一辆能折叠的儿童车,还有各种俄罗斯民间工艺品:本质的花漆小勺、小碗、成套的木制俄罗斯娃娃。因为有杨炳章给我的200美元,又加上接待单位给的生活补贴,我可以不太计较这些小玩意的价格。在当时,也可以算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从“儿童世界”回宾馆路程并不远,但因为买的东西太多太重,我还是叫了出租车,而且还得意地用俄语跟司机讨价还价:他要5美元,我还他3美元,第一次感受到了砍价的乐趣。
在莫斯科,我们还被邀请观看了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虽然语言不通,但那熟悉优美的音乐和高雅的气氛却是共通的。
离开莫斯科前夕,安德烈陪我们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在农庄的入口处,赫然排列着这个农庄在二战中牺牲者的塑像。他们是那样的年轻,全身充满英雄气慨。其实,俄罗斯人的英雄气慨和文明气质并不在艺术作品中,而且是随处可见的。在雄伟的莫斯科地铁站口,人们走路时总是昂首挺胸;在街头小摊前购物的人们总是规矩地依次排队;在公车上,人们自觉地打票,15戈比买一张;在公车或自己的私车上,他们从不大声喧哗,不乱丢脏物,也不随便吃东西。这一切细小的普通文明行为默默地证明着这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体现着这个国家的伟大和尊严,悄悄地感染着一切来访者,把美好的印象留在人们心中。
11月10日,我们怀着留恋之情提前告别了莫斯科。此行的遗憾是没有去列宁格勒,没有看到伏尔加河,未能乘国际列车穿越西伯里亚并眺望贝加尔湖。这使我有理由期待着再访俄罗斯。我希望这不是一个梦。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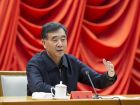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