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份胡耀邦和社科理论工作者谈话记录稿的发现
摘要:这是一篇内容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通篇谈话妙趣横生,完全体现了耀邦坦荡的胸怀和天真的性格特点。只可惜这次谈话后的62天,他就在邓力群、薄一波等人的大棒子下壮志未酬的离开了总书记岗位。
因为编过《胡耀邦年谱长编》,所以对搜集有关胡耀邦的资料就格外上心,这也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了。2010年底的最后一个周六我去潘家园转了一次,在一个旧货摊上发现了一份《胡耀邦同志接见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部分代表的谈话》记录稿的复印件,谈话内容是钢笔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稿纸上的,稿纸规格是:15行×20行=300字的稿纸,共12页,没有记录者的署名。当时粗略的看了一下,感到这个材料过去没有看到过,和摊主讨价还价花了10元钱就买下来了。回到家中细细的看了几遍,感到这份材料很重要,一是当年编年谱时知道1986年11月1日下午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的全体代表。也知道有这么个谈话,却没看到这个谈话的全文。
我查阅了线装书局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五册,在第5761页有对这次会议有明确的记载:
1986年10月29日至11月4日,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式和任务、制定和落实了“七五”期间的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三项决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由胡绳任组长,何东昌、朱厚泽任副组长;筹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共信息中心和全国网络;设立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基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会见了全体代表,并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一些成员和部分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胡耀邦说,繁荣社会科学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希望思想界、理论界要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寻求科学的答案;要把思想理论工作的基础打实在;要改进文风,理论著作要讲究表达方式,要充分说理;要多商量,多征求意见,以减少错误。
从以上公开记载的胡耀邦谈话的简要内容来看,这个记录稿肯定是这次座谈会的记录。现将记稿子全文录入如下:
胡耀邦同志接见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部分代表的谈话
时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三时半
地点——人民大会堂
中央的同志与社会科学界接触太少。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没有再接触过。今天和大家见面,我先谈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
繁荣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界同志们的愿望,也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理论工作一次大繁荣,是延安时期。这次理论繁荣使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那时以后,谈不上真正的繁荣。
现在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没有一个理论大繁荣能行吗?
理论与革命,理论与建设,可以说是互为因果。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推动理论发展;正确的理论反过来又指引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现在搞建设,应该争取使理论走在前头。
从历史教训看,理论确实非常重要。繁荣理论,是理论工作者的愿望,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更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
关于繁荣社会科学的困难和阻力。
任何事情都有困难和阻力。社会科学也不例外。问题是这种困难和阻力来自何处,必须弄清楚。
我认为困难和阻力要从两个方面去找。一是党的领导方面的缺点,二是理论工作者本身的弱点。
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碍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没有打下来。(李洪林同志插话:打下来了。)打破了一点皮,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
这方面的阻力今后还有没有?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但是,只要发现这种事情,就一定加以纠正。
(吴明瑜同志插话:已经有人被撤职,被赶到外地,被开除党籍。)
写报告来,我们就纠正。
(薄一波同志插话:被打的同志头皮要硬一点,顶住。)
妨碍社会科学繁荣的因素,除了领导方面以外,有没有我们理论工作者本身的某些缺点,弱点或不足之处呢?
我觉得加上这第二个方面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变成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薄一波同志插话:这个方面不仅理论界有,就是中央也有。)
关于党的干预问题,可以发个文件,或者多讲几次。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
为了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大有作为,我想提几条希望。请大家注意,这里不是提“必须遵守”。我只是做为一个普通党员向同志们提几条希望。
第一条希望是深刻理解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没写清楚,我们要再理解一下。
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讲透了,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毛病。
一种毛病是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药方。比如,从马克思的书上找出一个雇工的数量(按马克思为了论证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以变为资本,曾经设定一种剥削率,按照这种剥削率,至少要雇工八人,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结果这个数量竞成为我们今天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雇七个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个人资本主义。这能叫理论联系实际吗?
文艺方面也有这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地研究文艺理论。他们谈到过一些文艺问题,但是能说他们是文艺理论大家吗?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里寻找文艺理论的答案,恐怕不行。
总之,不要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找药方,那肯定要吃亏的。我们要从他们的书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不容易。要融会贯通,心知其义。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行了,要从西方去找真理。
我觉得两种倾向都不对。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认真学习,但是不要只向书本讨生活。西方的社会科学也要研究,但是不要迷信。我们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从这种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第二条希望是打好理论研究的基础。没有充分的资料,无法进行研究。过去说国民党没有准备什么资料。现在我们当权三十多年了,不能再怪别人了。
外国学者一方面批评我国没有材料,同时也批评我国学者自己不搞材料。我国的材料确实不多,已经有的还有不少要保密,这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有些第一手材料本身就不正确。比如中国耕地到底有多少?我们的数字是十五亿亩。可是美国的卫星测出我们的耕地是二十亿——二十二亿亩。我国的国土一向说是960万平方公里。美国卫星测出的是1040万平方公里。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如果弄不准,没法交代给下一代。
鲁迅写文章,材料都是自己准备。要向鲁迅学习。自己动手,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不再提“以共产主义为核心”。这个问题争论了好久。新的提法在理论上站得住吗?在组织上合法吗?没有扎实的基础,新提法是出不来的。
在理论研究上,搜集材料,分析综合,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这种思维活动,比体力劳动艰苦得多。
第三条希望是文风要改进。
理论文章没有味道,理论刊物人们不爱看。什么原因?有个文风问题。
理论文章要写得引人入胜,雅俗共赏,确实难度很大。要奖励优秀作品。文艺作品三年评一次奖,奖金一万元到三万元。我说太少,要三万到十万。理论著作也应该这样评奖,不过不能光由自己那一界来评选,要得到社会承认。
文风问题还包括充分说理。贴标签,打棍子,都不行。
(薄一波同志插话:真理挨得起棍子。)
真理不挥舞大棒,但挨得起大棒。
毛主席晚年之所以犯错误,首先是学风上有问题。不能把他的错误都归结成品质问题,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第四条希望是:为了使理论创作精益求精,少犯错误,要多商量。文章写出来不要急急忙忙发表,最好多征求些意见。
这几年,中央文件里面站不住的东西比较少,唯一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搞了二十个月,反复征求过意见。
中央的同志又自知之明。小平同志讲,就个人聪明才智来说,没有人能超过毛主席。但是靠集体智慧,就能更高明。
做理论研究,写文章,当然难免有错误。有了错误,进行批评和反批评,这就更好些。
中央是决不会打棍子的。
几年来打的棍子不是党中央的,这一点你们心中有数,不用我说。
好了。我一共谈了三大点四小点,可以说是不三不四。
(薄一波同志讲话之后,耀邦同志又补充了以下意见。)
最近我连续看《光明日报》的《胡适传》,应该写胡适传,也可以写得更好。
我还看了台湾作家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是以大陆为对象写的。看了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
前些天看了电影《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愈挫愈奋的性格非常感人。用“愈挫愈奋”来概括孙中山的一生,很恰当。宋庆龄临终前说我们对孙中山评价欠公允。
孙中山在他那个时代把西方先进的东西溶化为中国的东西,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写孙中山传,一两年不行就三五年。要写的真正能站得住脚,使子孙后代读起来受到教益。
毛主席传、周总理传,都应该写。
就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这个谈话相当不错。但是,他的基本的方法论,还是传统的,什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种老调唱了几十年,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怎样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所有的文件和决定都是“结合”,而且永远结合得正确。出了问题,就说没有“结合”,而是脱离了。
这是一篇内容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通篇谈话妙趣横生,完全体现了耀邦坦荡的胸怀和天真的性格特点。只可惜这次谈话后的62天,他就在邓力群、薄一波等人的大棒子下壮志未酬的离开了总书记岗位,而他的下属也没有躲过大棒子的挥舞,纷纷落马。
这次谈话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我想有必要把这次谈话内容公布出来,让更多的社会理论工作者体味耀邦当年对社科界的关注、对理论工作者的关爱。至于这份宝贵的历史文献是怎么流到旧货摊上的已无法考证,好在当年参加座谈并插话的吴明瑜、李洪林先生及与会的理论工作者大都还健在,关于这次谈话他们可能不会忘却,如果他们看到这篇记录稿也许能够勾起很多难忘的回忆。
(作者:史义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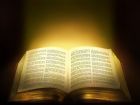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