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薛暮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摘要:倡导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这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但如何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于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
倡导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这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但如何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如何把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于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挑战。已过不惑之年的薛暮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货币与价格理论、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等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1980年,薛暮桥组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由于各项改革都会触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经济研究中心是咨询机构,不存在利益牵扯,因此,当时设计每一项改革措施高层就会习惯性地问一问:先问一下薛老怎么说。
1.要把“漏洞”改成“大门”
他是最早在理论界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如果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薛暮桥在一次会议报告上曾说:“过去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漏洞’,堵不胜堵,现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门。城市中不仅集体所有制还要提倡,连个体劳动,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补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详细)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节。时年75岁的薛暮桥正在杭州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期间,浙江上山下乡的回城待业青年到省府大院请愿,要求就业。无独有偶,当时,全国待业人员已经有2000多万,回城知青700万,留城待业青年320万。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城镇待业人员先后集会、游行、罢工、绝食、请愿、拦火车、进北京、写公开信,惊动中南海,成为“爆炸性问题”。
薛暮桥听说消息,提出要去现场。面对眼前的青年,他们身处大好年华却走投无路,无事可做,无业可求,令薛暮桥十分痛心。这不仅事关知青的前途,还关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会安定。而眼下,国家百废待兴,腾不出手来,也没有办法安置巨多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不从理论上找到问题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项具体管理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薛暮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从根儿上动。根儿在哪儿呢?根就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找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桥带着写好的书稿回北京,正赶上劳动部开会,邀请他参加并讲话。薛暮桥在1979年3月24日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谈谈劳动工资问题》,讲话中提到:
“理论界还有‘恐右病’,把资本主义当作瘟神,必须使它完全绝种。……目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点竞争,使国营经济减少一点官僚主义;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国营经济不愿干的事;第三,满足市场需要,方便人民生活。”“我们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管得太多,统得过死,国家不能帮助人家广开生产门路,又不准人家自找生产门路,把两只手束缚起来了,只剩下一个嘴巴张着要饭吃。人家看到门路可找,把手动一动,就是投机倒把,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比不过资本主义。”
薛暮桥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
北京市委有位负责人说:北京市的“资本主义漏洞”多得堵不胜堵,农民进城干零活一天赚两三块钱很容易。薛暮桥反问:“可不可以把这些漏洞向城市待业青年开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桥去中央党校做了一场报告,说:“有必要坦率地讨论我国现有的所有制结构。”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位外国公主到了机场愿出十美金请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没人干这个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是到了中国,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他提到过去车站、机场有人帮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还有搬家公司都办得好。
这个报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党校理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7月18日,《北京日报》摘要发表了这篇讲话,《北京周报》把它翻译成各国文字,《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也都转载。接着,《北京日报》开始了一场关于打破“铁饭碗”的辩论。薛暮桥的建议在北京地区首先试行。前门摆起了大碗茶、天坛开了燕京书画社、个体户挎个包或推个小车照相的生意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者一切税费全免。自薛暮桥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读者纷纷来信表示赞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问题请他解决。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由此起步。1980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终于逐步得到了解决。
2.“管住货币,放开价格”
物价改革是薛暮桥极力推动的制度改革。薛暮桥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和担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不改革僵化的物价管理体制、理顺价格体系,是不能正常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因此价格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82年,他曾就此问题与前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等专家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详细)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由国家统一定价的物价管理体制,整个价格体制越来越不合理。1979、1980年对价格体系进行过局部调整,主要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部分价格偏低的能源、原材料进行微调,并放开不少小商品的价格,但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还远未解决。
价格改革需要理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价格体系,另一个则是物价管理体制。1982—1984年,经济研究中心着重研究的是价格体系的调整问题,在研讨中大致形成了“大改”、“中改”和“小改”三种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兼顾各方面要求而又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综合性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可概括为“综合调整,调放结合,略有侧重,分步出台”,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意见和建议。
薛暮桥同志回忆这段讨论时说,对于调整价格,当时是有很大顾虑的,主要是担心导致物价总水平猛涨,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有关部门提心吊胆,迟迟不敢有所动作。当时火柴每盒2分钱,企业亏本,不愿增产,市场缺货,不得不限量供应。其实每盒涨1分钱,人民负担增加不了多少,却能迅速增加供应。这件事议论了多次还是不敢动手。薛暮桥等同志多次强调,防止物价总水平猛涨的关键,是要控制货币发行量,防止货币流通量过多。只要通货不膨胀,对部分商品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物价总水平可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总水平稳不住,根源在于没有管住货币。所以,薛暮桥等同志坚决支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制止通货膨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主张既积极又慎重地推进价格调整,可以先从条件比较成熟、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小的商品入手。
1982年当时我国的棉布因棉花几次提价而布价未提出现亏损;化纤布因化纤工业发展很快,成本下降,利润很高。物价局因怕化纤布降价影响财政收入,不让降价,致使产品大量积压,被迫减产。正好当年,经济研究中心正在研究棉花、化纤布调价问题。国家经委委托薛暮桥召开一次纺织品价格会议,他在会上大胆提出,提高棉布的销售价格,同时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以扩大化纤布的销路,代替棉布,使多年限量供应的棉布也可能敞开供应。薛暮桥说:“最好不要坐失良机,不要等化纤布降价降够后再提纯棉布的价格,并且尽可能使这项调价成为今后较大规模调整物价的突破口。”1983年薛暮桥同志患阑尾炎住院动手术,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去看他,他谈了再三考虑的意见,认为棉布、化纤布调价没有风险,可以出台。
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调价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又使化纤布得以放手生产。这次成功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
3.“要用银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
薛暮桥一再强调,“目前我国的银行不像银行,像个行政机关。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银行机关化,而要尽可能使它企业化。要用银行的办法来管理银行。现代化的经济,要有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实现经济现代化,银行要先行现代化。”(详细)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几年的金融改革,金融机构开始多元化,竞争局面逐步形成,但没有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在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设以后,人民银行还承担着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人们形象地说,人民银行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能处于超脱地位。各专业银行在利益驱动下,自我约束机制又不强,出现了抢占地盘、争放贷款的现象,导致信贷失控。早在1980年国务院领导就指示要设置中央银行,但是几年来没有取得进展。中国人民银行1982年5月提出《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的请示》,1983年1月提出改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设置农工商银行的意见。专业银行认为,这两个文件的实质是否定三中全会以来银行体制改革、设置专业银行的方向,以中央银行的名义恢复由一家银行独揽全部业务的局面,使专业银行名存实亡。
经济研究中心从1983年3月开始集中研究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先研究了各国金融制度的经验,并请前联邦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曾任德政府经济顾问“五贤人委员会”成员)来华交换意见,提出建议。1983年经济研究中心向国务院提出单设中央银行来管理各专业银行的建议,并提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严格管理货币发行,保证信贷收支平衡,不经营一般信贷业务。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委托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四大银行提出具体方案。
按照这一指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了12次座谈会。在薛暮桥第一次邀请四大银行开会时,由于过去相互间的矛盾很大,会上争执不下,以致会议无法结束。这时,薛暮桥请来了中心担任常务干事的徐雪寒。薛暮桥深知徐雪寒的价值。雪寒不仅经历过市场经济,而且有过经营银行的经历。在徐雪寒的协助下,分别邀请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的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背靠背的座谈。徐雪寒同志又到上海与四家银行的分行长、专家以及原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分别座谈,协调相互间的矛盾。
5月18日、21日,薛暮桥同志又邀请四大银行的代表和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的同志以及两位教授来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成立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要求运用银行筹集资金和外汇,提高投资效果。同时要求建立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确保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最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人民银行原来经营的工商业信贷和储蓄等业务,划归新设的中国工商银行接管。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就不直接经营信贷业务,只与专业银行发生信贷关系,真正成为“银行的银行”。这个建议经各银行讨论同意后,提请国务院讨论,并得到国务院认可。
4.从“分灶吃饭”到“划分税种,实行利改税”
面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带来的问题,薛暮桥再三思虑,认为应该采取“分税制”的办法。他主张,财政的分级管理要划分税种,同时要划分财政收支的分级管理。1983年国务院决定改“分灶吃饭”为划分税种,并实行利改税。利改税后,财政体制改革前进了一大步。(详细)
1980年开始,国家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大市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总额分成外,其他地方实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称之为“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加剧了中央财政收支不平衡。“分灶吃饭”后,中央财政收入缩得太小,不能保证必要的开支;财政体制的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不配套,“一定百动”,财政体制的基数和比例定死了,而经济上其他方面都在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盲目生产、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的弊病。这些现象过去就有,而在分灶吃饭、利润分成后,更难制止。比如,1981年国务院决定提高烟酒税率,原意是“寓禁于征”,结果各产烟叶地区反而争办小纸烟厂,很多县也争办小酒厂。小烟厂、小酒厂用优质原料生产劣质产品,使生产名牌烟酒的大工厂缺乏原料,被迫减产,造成很大浪费。薛暮桥认为,这是“分灶吃饭”、产品税由地方征收所产生的结果。
在薛暮桥的领导下,围绕着分灶吃饭,经济研究中心就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开展了多次讨论。1982年上半年,经济研究中心就进行了4次专题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财政部、计委、经委、农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大家认为,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财政体制的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也不能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必须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关系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问题,经济研究中心在下半年又组织力量做了进一步研究。在7月中旬,邀请辽宁、浙江、内蒙古、山西和湖南五省区财政厅预算处长和计委财贸处长开了小型座谈会。会后,与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共同联名向上级报了一份《关于改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只能前进,决不能再回到统收统支完全由中央集中理财的老路上去。但是,目前进行大的改革,条件还不具备。比较可行的是,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存利去弊,适当改进和完善分级包干的办法。
薛暮桥回忆说,在讨论过程中,财政部的同志主张财政体制必须改中央管理为中央、地方分级管理。他则认为应该采取“分税制”的办法,这才是正规的财政分级管理体制。薛暮桥主张,财政的分级管理要划分税种,有些税种(如重要产品的产品税)应由中央统一征收,有些税种(如所得税)应由中央统一征收、地方酌情留成,有些税种(如营业税)应由地方征收。同时要划分财政收支的分级管理。这种分税制的办法才是正规的财政分级管理制度。过去中央统一征收,地方从中央的大锅饭里打饭吃是不对的,现在地方分别征收,中央到地方的小锅里打饭吃也是不正常的。
经过反复讨论,财政部逐渐接受了薛暮桥意见。1983年国务院决定改“分灶吃饭”为划分税种,并实行利改税。利改税后,财政体制改革前进了一大步。但因价格没有调整,按同样的税率征所得税,各个行业苦乐不均。所以又对因价格偏高而盈利多的企业加征调节税。税种改革并未彻底完成。几年后又走回头路,改行逐级承包制,对此,薛暮桥曾几次提出反对意见。
5.外贸“统一管理、联合经营”
薛暮桥1980年去香港讲学时,看到对外贸易体制问题很大。薛暮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许多爱国华侨向他批评我们的外贸体制,询问他的意见,他说,对外贸易独家经营是不对的,但像现在这样多头经营也不行,应当改为“统一管理,联合经营”。(详细)
过去我们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是由外贸部的华润公司独家经营的,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不但不能直接经营外销,连国外市场价格情况也不知道,大家对华润公司意见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批准若干地区、部分企业可以有经营外贸的自主权。香港一下子成立了几十个(后来发展到几百个)外贸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削价竞销,互相竞争,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到1983年,外贸亏损在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据财政部统计,1983年上半年,全国外贸亏损已达42.53亿元,进口出口全部亏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进出口商品作价不合理,国内产品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由于货币汇率定得太低,外贸只能以进养出。其他原因还有:出口商品结构落后,缺乏竞争力,售价过低;“大锅饭”的外贸体制,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经营管理不善。大家认识到,如果不及时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对外贸易越扩大,亏损就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沉重。
后来,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周建南同志向经济研究中心提出了他的意见,说得不到外贸部的同意,双方意见有分歧,所以请经济研究中心来研究。1983年,外贸部向国务院报告了他们的体制改革方案,国务院否定了外贸部的意见,要求经济研究中心帮助外贸部另外制定一个方案。外贸体制改革牵扯到外贸部与中央各部门的关系、中央与各地区以及与各出口产品生产企业的关系、出口口岸与邻近各省的关系等,确实非常复杂。徐雪寒同志受薛暮桥同志之托,帮助召集会议研究,提出了“统一管理、联合经营”的方针。
开始时,外贸部担心提“统一管理”会受到各省市的反对,薛暮桥说,你们不敢提我们来提。在谈到“联合经营”时,外贸部又想走独家经营的老路。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在1983年国务院提出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对“统一管理,联合经营”是这样表述的:外贸部要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特别要管国外外贸机构的设置,对重要的进出口商品发许可证,决定各外贸专业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方针政策,协调它们之间的出口配额和价格等。至于进出口贸易公司的经营权,应当交给各专业公司。外贸部的专业公司与地方、部门的外贸专业公司以及生产出口商品的大工厂和专业基地,联合经营,各计盈亏。外贸部的各级专业公司,也应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各计盈亏,不要吃“大锅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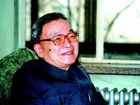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