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薛暮桥:冲破左倾“禁区
摘要: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但1977年和1978年两年间,全国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薛暮桥忧心忡忡,再三思虑之下,率先对以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为突破口,上书中央直陈利弊,试图冲破“左倾”禁区。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但1977年和1978年两年间,全国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薛暮桥忧心忡忡,再三思虑之下,率先对以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为突破口,上书中央直陈利弊,试图冲破“左倾”禁区。
1.忧心反思“洋跃进”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宣告结束。然而在薛暮桥看来,1977年和1978年这两年,纠正错误路线的工作徘徊不前,遇到了严重阻碍。对此,薛暮桥忧心忡忡。薛暮桥深深的感到,“只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不够的,还必须纠正过去20年的“左”倾错误,否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能走上正确道路的。”
在1978-1977年两年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倾向还在扩张。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80年全国1/3的县“建成为大寨县”。要求在3年内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要求当年有10%的生产大队升级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到处批判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在工业方面,提出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的高指标,要求建成以重工业为主的,120个大型项目,包括22个特大型项目迫使1978年基建投资猛增,并不顾国力盲目扩大国外引进规模。1978年,经济建设上出现了一次冒进,基建投资比上半年增长50%。
薛暮桥在粉碎“四人帮”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批评20多年来的“左倾”错误上,特别是经济政策的错误上面。在经过一系列的广范围、深刻的调研后,薛暮桥深深的感到,“只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不够的,还必须纠正过去20年的“左”倾错误,否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能走上正确道路的。”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薛暮桥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当时的助手吴凯泰回忆当时薛暮桥跟他讨论这个规划说:“这是要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他觉得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又上来了。当时,持续20多年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所以这些指示布置下来,好多人也都照着干了,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且敢说的人很少。薛老自己确实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到底说不说啊?”薛暮桥女儿薛小和回忆:“他开完会回到家,忽然就哭起来了。我问,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却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他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敲着扶手。我父亲是一个长于忍耐的人,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了忍不住的地步。”
2.上书中央,直陈弊病
薛暮桥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上书中央,倾诉他的意见。薛暮桥回忆道:“20多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错误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少数同志认识得早一些,但,往往还心有余悸,不太敢讲。要冲这个禁区,实非易事。”1978年4月18日,薛暮桥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同志,提出“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
这封信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农轻重比例和如何把农业搞上去。薛暮桥认为,导致农业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大办人民公社以外,主要实行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使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损害”。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民生活”。他“赞成农业机械化,但是要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益,确保机械化能够增产增收,不赞成一哄而上。”
第二,有关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体制。薛暮桥认为“在新的跃进形势中,中央建设项目的盘子又越来越大,地方工业、社办工业都在大干快上”。对此,他质疑“万马奔腾,会不会使现在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继续扩大?”他建议“在编制长期规划中,必须特别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务使各部门之间不平衡日益缩小,而不至于继续扩大。”
第三,总结历史经验问题。他认为“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他提出“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同志批评的”,“希望你们予以指示”。
薛暮桥当时的助手吴凯泰回忆:“后来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禁区,一个借调的同志就公开说,我可不参加。他显然是不敢冒这个险。”“他很清楚这些错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怎么犯的,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憋不住,他觉得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此信发出后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实际上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和加快农业发展得要求。
3.1000万册的心血之作
薛暮桥受到鼓舞,下决心冲“禁区”。他感觉总结20年经验教训,批评左倾错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需要写出系统的论著。1978年10月,他带领几位助手到外地专心写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这本书出版后,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在年逾古稀的75周岁之际,薛暮桥每天伏案8小时,3个月就写出初稿。以后经过两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到8月份最后定稿,年底出版公开发行。
鉴于本书出版时间偏后,在1979年年初到11月份之间,他给中央理论务虚会议另外写了题为“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20多年的经济工作”的书面发言,这个发言得到中央一些同志的赞许,并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除此之外,薛暮桥还在一些会议和地区做了几次报告,提前把这本书的基本精神扼要作了宣传。
这本书具体如实地说明当时许多同志尚不甚明了的经济建设的曲折经历与惨痛教训,批判了生产力发展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协调和稳定发展的错误,也批判了生产关系处理上急于过渡、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清一色公有制以及行政指令性经济管理体制。全书主要结论是经济工作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当前应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且探索和逐步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
该书成为薛暮桥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心血之作,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推动了当时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起步。“20多年的经济工作,他都亲身经历。此书系统详尽,许多原来本不了解20多年‘左倾’错误的人读了,也很信服。”吴凯泰回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于1979年12月,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与此同时,被译成日、英、法、西班牙四种文字出版。1980年初,《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经济新闻》的一条消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4.1979年经济调整之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贯彻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理论界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薛暮桥认为“这不是好主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薛暮桥感到,当时中央关于调整的决定贯彻的相当困难。原因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许多干部习以为常,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加之许多干部急于求成的情绪十分强烈,不少地区部门迟迟不下决心采取得力措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当时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实际上已经很严重了。第一,农业严重落后,按照人口平均粮食占有量大体上还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照人口平均的棉油占有量低于1957年水平。农业发展严重落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第二,轻工业发展滞后。基本建设投资集中投向重工业,对轻工业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78年仅为5.7%,低于“一五”时期的水平。第三,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过渡紧张。20%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第四,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将近20年农民平均收入和职工平均工资没有提高,积累率却一直在30%以上,1978年又高达36.5%。
针对这种情况,薛暮桥决心宣传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7月11日,他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指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来已久,现在已相当严重”。11月,薛暮桥给辽宁省委干部大会作报告时,批评1977年、1978年存在“左”的错误,1977年制定的十年规划凭空提出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主张“痛下决心”进行调整,坚决把6000万吨钢的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建规模,积累率最好保持在25%或略高一点,最多不超过30%。
报告的内容传到了国家计委,有的同志表示很不赞成,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积累率已经下降,“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也从14%降到8%,再要压缩投资,连简单的生产也难坚持”。薛暮桥回忆,国家计委内部也曾多次争议。1980年4月,在姚依林接任国家计委主任后的第一次党组会议上,廖季立也认为要“在压缩投资的同时,提高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薛暮桥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并提交了书面发言稿,主张切实执行农轻重并举的方针,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会后,姚依林把发言稿送到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去讨论。经过讨论,中央的决定是继续坚持贯彻调整方针。计委内部的争议最后停息。
调整和改革措施的实施,产生了它的最初效应。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一是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两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增加了近100亿元,而消费基金增加了580亿元。积累率开始下降,从1978年的36.5%下降到1979年的36.5%,1980年的32.4%。二是增加了城乡居民的收入,长期积累起来的生活欠账方面的尖锐矛盾得到缓解。1979年、1980年两年是建国以来增加收益最多的年份。通过放开农副产品收购和减免农业税收和社队企业税收,农民约得益300亿元。而且由于市场机制的初步引入,“经济搞活了”,短缺现象得到一定改善,市场出现多年少有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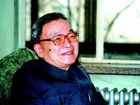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