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
摘要: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主要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人均GNI长期低于或徘徊在10000美元左右,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陷阱”至少包含两方面即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GNI低于10000美元。为深入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将通过对跨越国家和掉入国家的国际比较来说明这一现象。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主要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停滞,人均GNI长期低于或徘徊在10000美元左右,字面上理解“中等收入陷阱”至少包含两方面即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GNI低于10000美元。为深入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将通过对跨越国家和掉入国家的国际比较来说明这一现象。
一、“中等收入陷阱”是效率陷阱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时,通常用两类国家来进行比较:一类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1973年日本人均GNI为3580美元,仅用8年时间人均GNI突破10000美元跻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新加坡、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分别为12年(1977~1989)、8年(1987~1995)。另一类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在1986年、1994年、1991年人均GNI达到3000美元后,至今20年左右人均GNI没有突破10000美元,成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日本于1973年人均GNI超过3000美元,为3580美元,1980年人均GNI达到10860美元,超过10000美元而成为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为8年;与此同时巴西于1994人均GNI达到3050美元,2011年人均GNI达到10720美元,第一次超过10000美元,历时17年,是研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对巴西和日本1970~2011年间GDP增长率进行比较,除1987~1992年巴西GDP增长率明显低于日本外,其余年份均高于日本GDP增长率。与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相反,1970~2011年巴西的经济并非停滞,而是稳步增长,甚至在1971~1973年高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1.29%、12.05%、13.98%。
但两国的人均GNI在1970~2011年间差异却越来越大,1970年时巴西人均GNI为440美元,日本为1810美元,二者相差1370美元。到2011年巴西人均GNI10720美元,日本为45180美元,二者差距为34460美元,差距扩大24倍。
因而“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含义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人均GNI超过3000美元快速增长阶段之后,开始缓慢增长,以至于长期低于10000美元。高速增长率的背后隐藏着人均GNI的巨大鸿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呢?
李红艳等(2012)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统计的215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NI数据,对23个掉入国家和32个跨越国家农业生产工人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发现32个跨越国家农业生产工人的生产效率分别是23个掉入国家农业工人生产效率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和10000美元时的3.5倍和1.8倍,得出结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就是效率陷阱。效率观点代表了当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由低收入阶段粗放型向中等收入阶段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容否定,“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一个效率命题,即能否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人均GNI由4000美元稳定达到10000美元。
对巴西和日本净出口、投资、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发现,200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净出口占GDP比重均低于4%,2009~2011年巴西贸易逆差,净出口为负值。两国投资占GDP比重在20%左右,消费在GDP中占75%左右。因而效率的观点难以解释两国人均GNI的巨大差异。上述巴西与日本的比较可以看出,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但为什么巴西的人均GNI1994年已超过3000美元直到2011年才超过10000美元,17年时间尚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因而如果仅考虑效率方面,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公平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跨越国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1981~2010年间巴西的基尼系数均高于0.5,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个别年份甚至高于0.6(见图7-3),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不公平问题严重。而日本的基尼系数从1981~1990年间均低于0.3 ,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公平。
其他掉入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阿根廷自1986年以来,基尼系数始终大于0.4 ,2003年最高,达到0.5471,近年来系数有所下降,但仍高于0.4,超过国际警戒线。1986年该国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穷人收入的16.63倍,2001年达到58倍,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较为不公平。
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大都高于0.45,2000年达到0.51,而后略有下降低于0.5。1989年该国10%的富人收入是相同比例穷人收入的10.5倍,2000年达到27.7倍,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仍高于22倍,收入分配较为不公平。
相形之下,亚洲四小龙较好地重视社会公平问题,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发展战略,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1971年为0.36,1993年时仅为0.316 。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 ,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较低的基尼系数意味着社会各界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比较均匀,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国内消费,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同时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比较高,在0.4―0.64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大,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国内学者对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恶化不是导致拉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原因,但贫富差距恶化是关键性因素。发展经济学先驱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发生,以及它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就不可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布拉姆巴特(2007)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表明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公使得低收入者难以获得投资机会,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霍米?卡拉斯(2009)指出能否正确处理收入分配不公是印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2009年2月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说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严重性。2012年9月15日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农民工青年蔡洋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就是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一个最好注解。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因低收入引发的仇富心理已使其渐渐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引发的中国富豪移民、资本外逃问题,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对中国广大中低收入者而言,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物价上涨使得民生问题凸显,居民的幸福指数下降。
“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于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以牺牲社会公平的发展尤其牺牲大多数居民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最终会把增长扭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反之,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市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应该将社会公平放在首位,建立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机制,保障每一位居民都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教训比较给我们的启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找公平与效率“平衡”点,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仍然用“低收入国家”阶段以牺牲社会“公平”的发展尤其牺牲大多数居民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提高“效率”,最终会把增长扭曲,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反之,“公平”的社会环境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市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提高效率,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要继续维持“效率”,唯有突出社会“公平”,建立社会收入公平分配的机制,建设“橄榄型”社会收入结构,从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产生足够的推力,强劲助推经济跨越“陷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在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巴西等拉美国家人均GNI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仍过度关注GDP增长,忽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不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及时实现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虽然拉美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相差不大在70%以上,但拉美国家因为贫富差距恶化,广大低收入者、贫困人口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低消费结构进一步制约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的步伐,经济发展缓慢。只有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共同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
总之,“中等收入陷阱”既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能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从而使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大批贫民收入水平低下,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农村失去土地,在城市成为边缘人群,进而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秩序恶化、政局持续动荡。这警示我们,经济发展的内涵既包括较快增长,也包括合理分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没有持续增长,分配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合理分配,增长也会缺乏持久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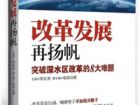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