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国务院立法28年
摘要: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最早始于1983年。28年以来,在税制领域,以“暂行条例”、“试行”形式颁布的税收条例“发展”迅猛。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却是凤毛麟角。
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最早始于1983年。28年以来,在税制领域,以“暂行条例”、“试行”形式颁布的税收条例“发展”迅猛。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却是凤毛麟角。
部分学者担心,税收立法权长期控制在行政部门,容易形成行政部门利用立法之便,进行税收扩张的立法与行政。2011年2月,车船税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被视为“一个好的开端”。
重庆市长黄奇帆5月28日关于房产税的一番言论,再次触发学界就授权国务院立法利弊得失的大讨论。
黄奇帆说,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将在1年至两年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完善,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后的“修改版”,可能在全国推广。黄是在重庆试点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满4个月时讲这番话的。
中国房产税征收依据是国务院制定颁布的房产税暂行条例,该条例于1986年10月1日施行。上海、重庆此番“试点”、“修改”,是将征收范围扩大到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
学者普遍关注到,在黄的讲话里,并未提及有关部门是否会在适当时机,将条例提交人大系统讨论、表决,并上升为法律。
全国人大系统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决定,最早出现于1983年。这一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就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工人退休、退职制定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其后一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国务院有权拟定税收条例,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改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此后,这种以“暂行条例”、“试行”形式颁布的税收条例,“发展”迅猛。本报记者了解到,截至2011年,中国已有21个税种,并且多数已施行近20年。
但与之对应的是,授权国务院立法28年以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税收法律,却是凤毛麟角。这其中,有公众耳熟能详的《税收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还有刚刚于今年2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次会议上通过的《车船税法》,在此之前,《车船税法》名为《车船税暂行条例》,此外即是正在审议修订中的《个人所得税法》。
28年来,学界发展出各种理论论证税法领域“条例多法少”的现象,有为之辩护者,亦有指出其缺陷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了这一现象在当时所具的合理性,“税制尚处改革过程中,倘若交由人大操作,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授权给了国务院”。不过,他也认为,(税制)长期由国务院进行规定,也不合适,税收毕竟是涉及全民义务,长期由行政机关定,就与依法治国相悖了。
近年来,学界担忧尤甚。部分学者认为,税收立法权长期控制在行政部门,容易形成行政部门利用立法之便,进行税收扩张的立法与行政。此前行政部门将燃油税并入消费税,借消费税之壳出台燃油税,而今又准备利用房产税之壳出台物业税,就是案例。
与之对应的问题是,在税制领域,出台条例容易,但上升为法律却步履维艰。实际上,在行政法领域,也存在类似难题。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例,该条例由拆迁条例演化而来,虽破天荒地经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仍未能走入上升为法律的程序。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副主任王才亮向本报记者透露,他自去年开始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不动产征收补偿法》。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亦曾向本报记者表示,国务院制定征收私人财产的法规缺少合法性,因为涉及“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不过,至今未见有立法动向。
回顾国务院授权立法这28年,我们能找寻何种利弊得失?这部分关切国计民生的基本法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缘何授权国务院制定颁布?而今,是否真如学界所述,到了回收部分立法授权的最佳时机?
“多条腿走路”
“授权国务院立法,与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立法长期停顿,改革开放初立法方面‘欠债’太多,国家立法机关又囿于自身人力、时间等条件限制,一时无法将所需法律适时制定出来并付诸实施有关。”烟台大学法理学教研室主任王春光说。
《人民日报》1997年的一篇报道,记录了当时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还缺乏实践经验,立法条件还不成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经验不成熟的不能立法,实际工作又不能等待。彭真同志经过反复思考,研究了几个方案,最后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授权立法。
张春生亦向本报记者回顾了当时的立法尴尬。他说,立法面临一些无奈,原因是中国发展太不平衡,这给中央层面的立法带来很多困难。有些法律好处理些,像刑法、民法,在全国都要统一执行同一个具体规范。但是,有的行政管理规范就难以完全统一,实行起来也有难度。
他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时候,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说要具体写上最低工资标准多少钱,有利于保护劳动者。但是细细研究,发现还是行不通。如果按东部沿海地区来定,西部欠发达地区根本做不到;按西部来定,东部又要吃亏。所以,劳动法里,最后只能写,第一,国家实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具体标准由政府定。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诸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法律里,经常能见到“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条款的原因之一。学界甚至一度认为,这是中国立法在回避问题。
张春生认为,交给国务院具体规定,相当于给国务院一个“小授权”,使之边实践边积累经验,一旦办法成熟,再上升为法律;还有些时候,是因为法律急着要用,对某个具体问题又确实找不到其他妥善的、成熟的方案,于是采取了这个办法。
正是在此思路下,1983年、1984年、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授权国务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这也拉开了中国“授权立法”的序幕。
学界普遍盛赞当时授权国务院立法推动了中国法治进程。王春光指出,国务院授权立法增多,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为国家正式立法积累了经验。
[page]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陈斯喜亦给予授权立法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立法凝聚了立法工作者的极大智慧:所有法律都让全国人大来制定,难以适应需要,所以就要多授权一些立法,“多条腿走路以加快立法步伐”。
不过,陈斯喜也表示,以前较多使用授权立法,包括专门作出授权决定,授权有关部门进行立法和在法律当中授权立法,“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后就要注意减少这种做法”,应更多地由立法主体直接立法,以保证立法质量和法制统一。
立法授权“一再加大”
陈斯喜的担忧,也许与立法授权一再加大以及授权立法行使过程中,逐渐出现问题有关。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陈颖洲对三次授权立法决定进行过研究,从第一次授权,到第二次,再到第三次,陈颖洲发现,立法授权是在“一再加大”。
第一次授权范围是安置老弱病残干部、工人退休、退职;第二次是工商税制;第三次,范围就开始“宽广”起来。
所谓的“第三次授权”,指的是1985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这一次授权,将授权范围扩展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当时,学术界对此给予了批评,因为其范围过于广泛,实际上国务院可以根据该决定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法,同时该授权决定的行使情况也令人难以知晓。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二局副局长万其刚则认为,这次授权依然还是较为审慎的。他认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所做讲话,实际上限制了这次授权的适用范围。
“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国务院方能)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如果同现行有关法律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则必须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王汉斌说。
更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授权立法行使过程中的权力“扩张”现象上。
王春光指出,被授权机关的所属部门(即部委),在无“再授权”依据的情况下,擅自行使本应由国务院行使的立法权,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举例说,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就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条例,被授权对象很明确是指国务院。“但在执行过程中,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委、国家税务局都先后制定过关于小轿车特别消费税的规定。”
此外,依据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决定,国务院拟定的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而实际上,国务院在对试行的税收条例重新修订甚至完全取代原来的税收条例时,并没有严格遵循授权决定的要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样,根据全国人大1985年作出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与条例的决定》的规定,国务院依授权制定的法规必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可这一程序性要求,也并未得到有效遵守。
“一个好的开端”
授权立法一再加大,以及其本身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原本有望在《立法法》制定后得到解决。可实际上,《立法法》并未起到定纷止争作用。
2000年7月起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明列九类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其中包括: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按此规定,居民个人住房既是“非国有财产”,对其征税又属“税收的基本制度”,因此,对个人住房征税受《立法法》“只能制定法律”中的两项约束。
但《立法法》第九条又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学界认为,第八条与第九条中存在的矛盾,让《立法法》“只能制定法律”的条款大打折扣。
而《立法法》中所存矛盾,也成就了近年来“部门利益”侧身于立法过程之中。本报曾报道过的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进程一事,就是一例。
在《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前(自然遗产保护法目前仍处于立法进程中),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保护领域,还只有国务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学界为此几乎每年都疾呼加速立法进程。
可饶是在此背景下,自然遗产保护法7年修改超10次,仍旧难产。原因是“我国遗产资源因部门利益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各不相让: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主管自然保护区,其中多数包含自然遗产;国家文物局主管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文化部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住建部以风景名胜区名义既管理自然遗产又管理文化遗产;国家旅游局则以旅游统管遗产经营……
张春生指出,政府部门争取部门利益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政府的部门有权,手里又有资源,他们的声音容易在立法机关里反映出来,“中国30年以来的立法程度不等地存在这个现象”。
不过,也有学者欣喜地看到,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前后,这一现象,逐步有了规范化的趋势。
根据新华社2007年6月28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赞成授权国务院可以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停征、减征个人所得税,授权的方式以采取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二条的方式,不采取以往惯例式的国务院提议授权决定形式。
而在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甚至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工商税制授权决定。这是时隔25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废止授权国务院税收立法的决定。
但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决定,依然有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解释说,依据1985年的此项授权,国务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暂行条例,这个授权决定已将1984年的授权决定覆盖。而1984年的授权决定主要是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营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问题。
“1985年的授权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改革初期,为了适应形势快速变化而做的临时授权。但现在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从应然角度看也应取消,并逐步按照正常程序让人大来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说。
俞光远认为,授权立法是由于全国人大人员编制限制,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难以应付大量的立法需求,但政府主管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又可能会把主观愿望带入法律中,导致立法产生倾向性。因此,为解决这些现实的难题,可由全国人大牵头,主管部门参与,由人大和主管部门联合起草法律,提高效率,逐步改革。
“长期来说,全国人大的立法力量应该加强。”俞光远说。万其刚则关注到,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车船税法,车船税由此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万其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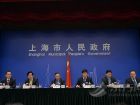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