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笔
摘要: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
那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事宜:“(一)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十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
《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作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中宣部、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说,《毛泽东选集》书前的《本书出版的说明》是他写的。文末本来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于考虑到“编辑”两字似乎不妥——毛泽东的文章还要由别人“编辑”?于是他改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此后,便一直沿用这一名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一些文章,经毛泽东阅定后,在出版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便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第四卷在胡乔木主持之下,与前三卷不同,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第四卷的许多题解以及政治性释文,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编辑及定稿工作,在1960年二、3月间进行。1960年9月下旬,第四卷出版发行。
胡乔木为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了大力。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党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共党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21日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杨尚昆曾经这么忆及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语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共党史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三人。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胡乔木那时还有一个兼职,即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文教委员会直属政务院,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据林默涵回忆,文教委员会下设一个计划委员会,最初内定林默涵为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消上报、批准就行了。
然而,出乎意料,胡乔木反对此议。
一天,胡乔木跟林默涵一起散步。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要安排你当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深,你当副主任不合适……”
胡乔木这话,当然使林默涵心中颇不舒服,不过他毕竟还是听从了胡乔木的意见。
不久,计划委员会的正式名单公布了。林默涵一看,跟别的委员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在北京城外工作。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城外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那时交通不便,她只能一星期回城一趟。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十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诸多不便。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林默涵深为胡乔木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胡乔木的兼职不少,他受毛泽东委托,还兼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
1951年7月10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中共中央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拟在五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会议也讨论了毛泽东的俄译稿事宜,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人(均精熟俄语,又有理论修养)校阅。会议提议组成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负责。然而,王稼祥一再推辞。
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7月13日致函胡乔木,考虑到胡乔木英语不错,要他暂且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的工作。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7月13日
胡乔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
1953年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策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简化。”
会议的新闻稿,由胡乔木转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5月22日致函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
马部长:
此件(引者注:指会议新闻稿)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1953年5月22日
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还要兼顾并主持着中宣部的工作。诸如中宣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也由他主持拟定,于1951年1月15日向毛泽东递送报告。翌日,毛泽东便作了批复: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11月16日
江青,原本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时亟想“露峥嵘”,先是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6至7月,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去山东堂邑一带,从调查武训的历史入手,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回来后,这个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于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武训历史调查记》)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7月11日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江青越发得意,企望着走上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就把原本拟安排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改为副处长。
又是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又得顾及文字改革和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还得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主持新闻总署,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的工作头绪甚多。即便如此,胡乔木还不断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诸如: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1950年11月20日社论):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1951年元旦社论):
《评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8月11日社论);
《印度缅甸拒绝签订美英对日和约》(1951年8月29日社论);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1953年元旦社论);
《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12日社论……
在杭州起草《宪法》
胡乔木忽地要离开北京。
1953年12月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了请示信:
“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
为此,毛泽东于12月10日在胡乔木的信上,作如下批语——
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
(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毛泽东12月10日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刘、周、朱、陈、高”,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前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当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文字问题”,是指由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汉字改革及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两个文件。
胡乔木为什么要离京?他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因为又降重任于他肩上——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2年12月24日,在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着手起草宪法。全国政协常委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提议。于是,宪法的起草工作,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亲自挂帅,主持宪法起草工作,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只是1953年因部分省市受灾,政务院发出救灾工作指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推迟至1954年召开,宪法的起草工作也相应推迟。
宪法是根本大法,起草工作也就很慎重。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初稿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后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小组由八人组成,即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实际上,真正动笔起草的,在这八人之中,显然是三位“笔杆子”——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均为毛泽东秘书。
为了避开北京冗杂的事务,便于专心起草宪法,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于1953年12月24日来到杭州。
起草小组通过内务部,搜集了许多国家以及中国往昔的种种宪法。胡乔木一时间完全“进入角色”,钻进了宪法堆里,反复钻研着种种宪法,内中有:
1918年苏俄宪法;
1936年苏联宪法: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
1946年法国宪法;
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亦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
1923年曹锟宪法;
1946年蒋介石宪法;
……
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一文中,这么写及在杭州的工作情形:
“1953年底,毛主席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准备去杭州起草宪法。陈已先拟初稿,听说又要别人参加,改动他的稿子,就已很不高兴。到杭州后,陈告诉家英,他要住在北山高处,表示他不负任何责任。第一次开会讨论,他又对家英发火,认为任何人非经他的许可,不得在主席面前讨论原稿,并且不许向主席说明会中原委。家英对陈的这种专横行为非常愤慨,却无法反抗。此后,每次开会以前,先得向陈做一次汇报。直到罗瑞卿后来(他是一道来的,但以前并没有参加起草宪法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提出某某条应该这样改,某某条应该那样改,陈管不了他,陈独裁的局面也就打破了。陈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到杭州来,来了势必改动他的原稿,加上讨论时毛泽东自己也常常当面对陈的草稿提出种种重大的修改意见,所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闷闷不乐,常对家英说:‘我不行啦,要回老家当小学教师啦’,等等。”
胡乔木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与他及田家英的矛盾。
参与过起草《共同纲领》的胡乔木,对于起草宪法已算是有了经验。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1954年2月中旬,起草小组写出了初稿;2月20日,写出二读稿;2月25日,写出三读稿;3月8日,写出四读稿。
3月12、13、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大体上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此后,草案交各方广泛讨论,八千多人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直至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宪法》的序言是由胡乔木执笔的。胡乔木也参与了其他部分的起草。
不过,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后,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压到了田家英肩上。胡乔木离开了起草小组。
胡乔木又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次病倒
胡乔木到苏联去了!
繁重的工作,使胡乔木又一次病倒。这一回,他的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先是在北京住院治疗,不久送往苏联,住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
在那里,闹了笑话:苏联大夫进病房,嗅到一股臭味。细细找寻,发现胡乔木带来了发出臭味的东西——在玻璃瓶里,装着白色的小方块食物,长着灰绿色的霉斑,臭气冲天。大夫双眉紧皱,把玻璃瓶扔进了废物箱。胡乔木深为惋惜,因为那是他特地从国内带来、喜欢吃的臭豆腐!
胡乔木病了之后,承受工作重担的田家英也累倒了。虽然田家英比胡乔木小十岁——那时只有三十二岁,累得吐血了。
对于“秀才”来说,眼疾对工作影响最大,不能看书、看报、看文件,也无法从事写作。不得已,胡乔木只得放下笔杆子,专心休养,又度过了一段“空白期”。
眼疾日渐康复,胡乔木的笔,重新忙碌起来,帮助周恩来起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9月1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即政府工作报告)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毛泽东9月19日
过了几天,由胡乔木写的《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作为《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于1954年10月1日发表了。这表明胡乔木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
此时,他又多了一项任命: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为邓小平。
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曾经从来福堂迁至喜福堂,这时又迁至颐园的一座四合院。从此,他在颐园一住十二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逐出中南海。
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参与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种种重大事件。
他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1955年3月1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
即送胡乔木同志:
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毛泽东3月12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此件”,即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他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在1955年6月6日致函陆定一、周扬——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
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泽东6月6日
他还参与了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的修改工作。前者,是由陈伯达起草的。
1955年9月6日,毛泽东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尚昆同志:
此两件,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告胡乔木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
毛泽东
9月6日零时半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除了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之外,还曾为周恩来总理起草重要文件。谷羽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4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这篇文章便是著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中共和苏共产生严重的分歧,是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
2月24日夜,苏共“二十大”举行重要会议。苏共没有请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其中也包括中共代表团。虽说他们事先向中共代表团打了招呼:“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对于别的党就不一样了。只是不便于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请你们原谅。”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夜。赫鲁晓夫通宵达旦作了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苏共倒是真的没有把中共代表团当成外人。很快的,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送给了中共代表团。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地否定了斯大林,批判了个人崇拜,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震动。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由于团长朱德还要继续出访,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由邓小平带回北京,毛泽东读了秘密报告震怒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为之震惊了。
毛泽东指出苏共“二十大”两大原则性错误:其一,全盘否定斯大林;其二,所谓从资本主义“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的“离经叛道”的行径,决定公开予以驳斥。
毛泽东嘱咐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阐述中共的观点。于是,陈伯达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于1956年4月2日打出清样。毛泽东嘱“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然后于3日下午召集上述人员开会讨论,进行修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本是《人民日报》社论,临发表之际,毛泽东改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亲笔在标题之下,加了这样一句话——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篇长文于1956年4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首次开始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引起世界瞩目——虽说行文是婉转的,只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中共与苏共意识形态差异。
那时,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理所当然地使资本主义阵营为之兴高采烈。
于是,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于是,胡乔木奉毛泽东之命,写了题为《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于1956年11月3日发表。
胡乔木写道: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最重要的支柱。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的一致,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兄弟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虽说中苏双方都强调了“友谊”、“合作”、“团结”,而且还强调这是“万岁”的,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正日益加剧。于是,就在那篇“团结万岁”的社论发表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此文按照类似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讨论范围加以讨论。发表时,仍照前例,在标题之下加了一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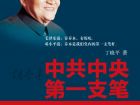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