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红色之路
摘要:胡乔木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默默地做着。他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正因为这样,他的身世,在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才由新华社播发他的数百字的简历。此外,笔者也只查到1949年10月,当他出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兼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及上海《新闻日报》登过关于他的经历的简短报道。长期以来,他主管宣传工作,没有他的点头,难以发表关于他的报道,而他向来不愿宣传自己。如此这般,他的身世就变得鲜为人知。
走上红色之路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
胡乔木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默默地做着。他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正因为这样,他的身世,在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才由新华社播发他的数百字的简历。此外,笔者也只查到1949年10月,当他出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兼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及上海《新闻日报》登过关于他的经历的简短报道。长期以来,他主管宣传工作,没有他的点头,难以发表关于他的报道,而他向来不愿宣传自己。如此这般,他的身世就变得鲜为人知。
他的夫人谷羽,跟我谈起了他的老家和最初的经历。不过,她说胡乔木的胞妹方铭比她更熟悉。于是,我去访问方铭。
方铭在1992年时,已经七十有五,长相颇像胡乔木。她的身体不算太好,她的丈夫那几天又因发生中风征兆急送医院。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仍抽时间很详细地向我介绍胡乔木。特别是第一次谈话后,她颇为劳累,头痛不已,睡眠不好,但还是约我继续再谈……
方铭,原本是她进入延安时改的名字。那时,她读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非常敬佩,遂取名“方铭”——把方志敏铭记于心之意。她本名胡文新,胡乔木的二妹。
胡乔木兄弟姐妹五人,胡乔木居中。
大姐胡履新,如今居于北京,能自己料理生活,退休干部。笔者见到了她,白发苍苍,但行动仍很灵活。
大哥胡达新,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解放后曾任西安铁路局副总工程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胡乔木受到“审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胃部常常疼痛不已。经检查,患胃癌,1972年病逝。
胡乔木是老三,原名胡鼎新,取义于成语“革故鼎新”。虽说他直至进入延安才改名乔木,此前一直叫胡鼎新,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笔者行文仍称之胡乔木;
大妹胡穗新,现名胡夏青,离休干部,曾任天津某中学校长,后在北京某中学任校长。现住北京。
小妹胡文新,亦即方铭,离休干部。
壬子年(即民国元年)4月16日,亦即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省盐都县鞍湖乡张本庄。
盐都县属盐城。盐城是江苏省的省辖市,位于苏北大平原东部,濒临黄海。盐城市下辖城区、东台市、大丰市、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建湖县、射阳县、盐都县,共九个县(市、区),总面积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
盐城盐、渔、农业较为发达,尤以产淮盐著名,因而得名盐城。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胡乔木的出生地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
胡乔木之父,乃盐城名流。人们习惯地称他为胡启东。方铭说,其实启东是他的号,他的名字是胡应庚,生于1885年。父亲给予胡乔木的影响是深刻的。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是受了父亲的感染。
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
胡家本是农民。到了胡启东这一代,已有五十来亩土地,是地主了。
如今,胡家的盐城旧居,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旅游景点之一,人称“胡乔木故居”:
胡乔木故居原为砖瓦结构的四合院,前后三进,连东、西厢房有数十间。土改时,胡乔木父亲胡启东先生,主动将田地、房产献出,分给贫佃农,仅留下座北朝南堂屋三间。1991年当地政府对故居进行了重新修建,现有故居占地约200平方米。
故居堂屋正中悬挂着胡乔木七十岁时的巨幅画像,两侧悬挂的是他在北京工作、生活时的数十张大幅照片,其中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合影十余张。东房间陈列着胡乔木生前捐赠的千余册图书,西房间陈列胡乔木幼时睡的床铺,用的部分桌凳,还有原全国书法协会领导成员,标准草书学社社长胡公石赠送的28幅诗词字画。在故居东南方,还保存一高大石碑坊,上边横额是“贞孝之门”,两侧有联,为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手书,联曰:
春祠立石垂视范,河客停桡拜女宗。
这是当地百姓为表彰胡乔木祖母胡季氏青年守寡、抚孤成立而捐资建立的。
胡启东小时候,家境尚不宽裕。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读书:那是同村的一户有钱人家,请了私塾教师教儿子,想找个孩子伴读。胡启东与他儿子年纪相仿,聪明伶俐,便被选去伴读。从此,胡家与诗书结交。
胡启东居然考上了秀才——清朝的末届秀才。回乡,做私塾教师。娶妻夏氏(不知其名),亦即胡乔木之母。
胡启东的诗文不错,在当地有了名气,成为盐城名流。民国初年,成立国会。这首届国会于1914年1月被袁世凯解散。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胡启东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二届国会议员。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护法。胡启东也南下广州护法,站在孙中山一边,在当时算是进步、开明的绅士。他在广州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下诗集《寓穗集》。
胡启东在1923年10月,受到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那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然后在国会举行选举,以五千元收买一张选票,要议员们选举曹锟当总统。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10月5日选举时,出席的议员五百八十七人,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那些受贿的议员,被人们咒骂为“猪仔议员”。胡启东拒收贿款,不投曹锟的票,不当“猪仔议员”。他回到了故乡盐城,受到父老乡亲的敬重。
此后,胡启东告别宦途。他曾受命续修《盐城县志》,当地人称之“胡氏县志”。他家的田,由五十多亩增至一百来亩。当胡家长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家境更好些,土地增至二百多亩。
胡启东喜欢写诗。他曾自费印行诗集《鞍湖诗集》。胡乔木也爱写诗,是与受父亲的薰陶有关。
胡乔木在六岁时进入鞍湖小学(今张本小学)上学。那时,他穿一件黑色的粗布褂子。他读书很用功,而且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夏日,在帐子里看书。只是他不喜欢体育运动。
胡乔木的学习成绩不错。在鞍湖小学读了六年,毕业时受到校长当众表扬——因为他的毕业成绩荣居榜首。
1924年,十二岁的胡乔木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今扬州中学)。他是鞍湖小学那年唯一考入江苏八中的人。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江苏八中,一所学风严谨、教育质量很不错的中学。今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之中,有十多位便出自该校。
江苏八中的左翼势力也颇强。1926年冬,江苏八中的学生们上街宣传,胡乔木也参加了。胡乔木在讲演时,点名批判了军阀孙传芳,为此遭到逮捕。鉴于他年幼,不过十四岁,很快获释。此事表明,年纪轻轻的他,已是左翼阵营中的一员。
他的大哥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学习,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胡氏兄弟都热心于政治。
恽代英来到江苏八中演讲,给学生们莫大影响。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江苏武进县人。他的演讲,富有鼓动性,使学生们为之振奋。胡乔木也是热心的听众之一。
从此,《中国青年》杂志成了胡乔木的密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发行量达三万多份。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担任编辑,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在延安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这足以表明,当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当年该刊主编恽代英的演讲,给予胡乔木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中共在这所名牌中学建立了组织。胡乔木读到了《向导》。《向导》是中共中央刊物,周刊,半公开发行。胡乔木在《向导》上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罗章龙等的文章。他也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军阀孙传芳占领了扬州,抓学生当兵。八中的校长叶维善决定学校停课,让学生们回家躲避。胡乔木随哥哥胡达新到镇江住了些日子。当他返校时,江苏八中已改名扬州中学,他进入了高中一年级。
高中分文科、理科。那时的胡乔木学理科,却又酷爱文史。他给校刊写诗,被吸收为校刊编辑。
1929年江苏大旱,胡家收不上租来,经济困顿。那时,胡家五个子女,有四个在上学。不得已,胡乔木则不得不休学,以便省下钱来供大哥胡达新上完大学。
失学,对于胡乔木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幸亏校长帮了他的忙。校长教化学,让胡乔木做他的助手,批改实验作业,给他一些钱。这样,胡乔木在半工半读中读完高三。
临近毕业时,校方开除了几名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胡乔木为此写信给学校教务长,批评校方“甘当国民党的工具,把无罪的同学开除了……”这表明胡乔木的政治态度已很鲜明,表明他与共产党人有很多联系。
1930年夏,十八岁的胡乔木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胡乔木进入清华大学,有人说是读中文系。其实那是误传。前些年,方铭生病住院,正巧胡乔木也住院。病中闲聊,胡乔木向方铭说起了他进入清华大学的有趣的经历……
胡乔木在高中读的是理科,也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时,系主任乃大名鼎鼎的吴有训教授(后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生入学后,吴教授便找新生们谈话。他问起胡乔木喜欢读什么,胡乔木照实直说,说的都是文史方面的课程。
吴有训当即说道:“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读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吴有训的一句话,使中国少了一位未来的物理学家,却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于是,胡乔木转到了文科。不过,他没有进中文系,而是进历史系。那时,中文系的招生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余额,而胡乔木对于历史也有兴趣——此后,他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直至晚年提议编写并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都跟他当年读过历史系有点瓜葛。
传说胡乔木进入中文系,大抵是由于他跟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教授有过交往。
朱自清虽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但自五岁起便随父母迁往扬州,在扬州长大,他自称“我是扬州人”。在扬州中学上高中时,胡乔木便细读了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对这位散文名家钦慕不已。
进入清华之后,清华的左翼力量颇强,学生会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中。胡乔木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活动。他给朱自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征询朱先生对于“左联”的看法。
朱自清曾是中国文坛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1926年3月18日,朱自清教授曾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向当时的“执政府”请愿。军阀政府下令开枪,他亲历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然而,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埋头于书斋做学问。他收到胡乔木的信,出于对这位扬州中学毕业的“半同乡”的情谊,亲笔复了一函。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但据胡乔木回忆,大意是:
大道之行,势不可挡。我或同情下去,或消沉下去。请来寒舍一聚……
寥寥数语,勾勒出朱自清芜杂的心境。他既同情左翼文化运动,以为“势不可挡”,但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他约见胡乔木,对这位青年学子说及自己的夫人武钟谦不久前病逝于扬州,也说及自己准备留学英伦、漫游欧陆……
1930年底,十八岁的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
据曾迪先之子曾昭凯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曾迪先,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起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夏,因白色恐怖,离开北平。胡乔木那时是我父亲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并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1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在曾迪先的帮助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里的活跃人物。他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发展了团员,组成两个农民团支部。
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干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共党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以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子。
他们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后来在1974年至197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他比胡乔木小一岁,盐城同乡——1913年2月出生于盐城庆丰乡东乔庄。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到盐城的教会学校准美中学上学。后来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胡乔木和乔冠华有着同乡、同学之谊。
乔冠华帮助胡启东找到了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既没有在大学学习,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何况生了病。他就向组织请了假,随父亲暂且回老家盐城。
就这样,胡乔木在1932年春回到家乡。
姐夫张肃堂在盐城宋村中学教语文。胡乔木来到那里,帮助姐夫教课,改作文,度过了一个学期。
胡乔木的三姨父,在盐城县城当贫儿院院长。秋天,胡乔木到三姨父那里,帮助他办贫儿院。那里有一位教师叫刘必余,很注意胡乔木。他从胡乔木的言谈及所看的书籍判断,胡乔木是个左翼人物——胡乔木从北平回到故乡,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
刘必余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向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作了汇报。嵇荫根决定找胡乔木谈话。谈了几次,胡乔木明白嵇荫根的身份,喜出望外:因为他自从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后,曾给北平中国大学一位姓陈的同学去信,那位同学是共青团员,胡乔木希望恢复组织关系。无奈,去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那个同学已离开中国大学。他想不到,中共盐城县委会主动找他,于是他详细陈述了自己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经过……
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作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胡乔木在镰刀铁锤大旗之下,奋搏了一生。
胡乔木加入中共之后,依然做他擅长的工作——宣传。他在盐城创办了《海霞》半月刊,三十二开,宣传反帝反封建。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只是他不便出面,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担任主编。那时,乔冠军是当地小学教员。
胡乔木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著作的英译本转译了小说《凡卡》,发表在《海霞》上。
《海霞》出了三期,便陷入经济困顿的窘境。盐城毕竟是小地方,《海霞》成本高,售价也高,销路不好。
看来,办杂志不行,那就改办报纸性刊物——《文艺青年》。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价格比《海霞》低得多,销路也就好一些。《文艺青年》是周刊。为了使刊物有上乘之作,胡乔木特请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还翻译、发表了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胡乔木的苦心经营下,《文艺青年》出了五期。
胡乔木还发展了邱剑鸣(胡扬)入党,发展妹妹胡文新(方铭)入团。他起草了《告盐城人民书》,油印成传单,和邱剑鸣以及妹妹胡文新等在深夜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
盐城的国民党政府注意起中共的地下活动。胡乔木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阜县委书记(那时中共盐城及阜宁县委已合并)嵇荫根被捕,很快就叛变。嵇荫根供出了两名中共党员之后,便带人直扑贫儿院,去抓胡乔木。
贫儿院的门房不错,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去告诉胡乔木。知道情况不妙,胡乔木急忙躲到贫儿院隔壁邻居家的床底下。贫儿院的院长、胡乔木的三姨父出面,跟嵇荫根周旋。三姨父声称胡乔木绝对不会是共产党,况且眼下又外出了。嵇荫根虽明知胡乔木是中共党员,无奈搜遍贫儿院找不到胡乔木的身影,只得勒令胡乔木的三姨父写下“保证书”。
这么一来,胡乔木难以在盐城立足,悄然南下,避往上海……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父亲胡启东希望胡乔木还是上大学为好。胡乔木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于1933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
就在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不久,一份名叫《沙泉》的壁报,引起了校长郭任远的注意。就壁报的内容而言,虽然带点左翼的色彩,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校长的目光,凝视着壁报上的一张图片。这图片显然是从什么现成的报刊上剪下来的,那是一位苏联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论图片内容,似乎也没有太犯忌的地方。然而,郭任远却看出,那图片显然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的!
郭任远追查《沙泉》是谁编的。一查,编稿、写稿、抄稿,由胡鼎新一人包揽。
上一回,是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谈话;这一回,则由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找他谈话。
郭校长直截了当:“你那图片,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而该报是共产党办的。你从哪里弄来《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故作惊讶:“《中国论坛报》是共产党办的呀?我不知道。我在路上拣到一张报纸,见到这图片不错,就剪了下来。”
从此,那“沙漠之泉”——《沙泉》被取缔了。胡乔木也受到了注意。
那时,他从盐城仓促出走。在上海,他遇见同乡陈延庆(王瀚)。陈延庆手中有中共地下刊物《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到了浙江大学,单枪匹马办起了《沙泉》。那图片,是从陈延庆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
胡乔木不办壁报,在外文系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秘密地组织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由于都是外文系的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
后来,学校里发现共产党印发的传单。校长郭任远又找胡乔木谈话。显而易见,校长已经“盯”上他了,尽管那传单并非他印发的。
1935年,一桩小事诱发了浙江大学一场风暴:两个大学生在打网球,两个教员也想打网球,便赶走学生。学生以为教员太不讲理了,争了起来,以致打了起来。教员告到校长那里,郭任远下令开除那两个学生。这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全校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跟郭任远对着干——那委员会又称“驱郭委员会”。胡乔木是主要成员之一。郭任远斗不过学生们,只得表示辞职。
胡乔木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郭任远开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胡乔木作了精彩表演。他来了个反话正说,含着“眼泪”,大声地诉说:
“我们敬爱的郭校长要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长真好,他那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提倡打网球!他又那么关心我们的壁报,连一张图片都仔仔细细地看,还要弄清楚图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郭校长实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学全体学生都哭了!”
台下,一片哄笑,同学们笑出了眼泪!
郭任远恨透了胡乔木,搞了个小动作,把胡乔木的成绩从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于是,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头,勒令胡乔木退学。
这时,教务长费巩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乔木谈话,给他开了“休业证明”,帮助胡乔木转学。
于是,胡乔木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也真巧,当胡乔木被浙江大学勒令退学,来到上海,妹妹方铭在苏州也遭勒令退学,来到上海。
方铭那时在苏州中学上学。1935年“三八”节,方铭在学校里张贴壁报,介绍蔡特金,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于是,学校勒令她退学。
她跟二哥胡乔木一起,在上海闸北江湾路租了房子,住了下来。
胡乔木很快跟那个寄《中国论坛报》给他的同乡陈延庆取得了联系。陈延庆高高的个子,人们总是喊他“大陈”、“长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上海东区区委委员。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大陈”带着胡乔木,来到“社联”。“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陈延庆当时都是“社联”的领导人物。胡乔木参加了“社联”工作。不久,胡乔木担任了“社联”常委。
“社联”乃“文总”的下属组织。“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中共领导下于1930年7月成立。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下属组织除了“社联”外,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总”还创办了《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凌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布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颇久,这位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里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著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里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峰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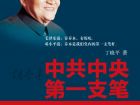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