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摘要: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
199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前来北京三○五医院: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来医院。接着,常委李瑞环来了。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了。江泽民未走,国务院总理李鹏赶来了。
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为一位外宾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在晚宴之前,抽空前来。
三天前,9月14日,薄一波和邓力群前来医院。
邓力群曾回忆说:
他(指乔木同志)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两天后,9月19日,上午姚依林来,下午陈云、王震派出秘书来。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来。
他们都来探望一位病危的八旬老人。老人戴着氧气面罩,病情沉重,但头脑尚是清醒的。三○五医院在9月12日发出了他的病危通知。
9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讣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七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枝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毛泽东是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谷羽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胡乔木这“中共中央一枝笔”的一丝不苟: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被称作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人所瞩目。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笔下;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第二版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他的一生,写了大量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延安《解放日报》或后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确确实实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胡乔木这枝笔,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笔者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1992年11月30日采访于北京。,据他回忆,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他说起胡乔木:
“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正因为这样,在胡乔木病重之际,陈云派秘书转达了他的问候,并且表彰了胡乔木这枝笔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
胡乔木的一家
胡乔木去世后近一个月——10月26日,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过的延安地区。
后事已毕,他的亲属们渐渐从哀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答应接受笔者的采访。我从上海前来北京,步入胡宅,来到胡乔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茄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
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的办公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叠文件,一望而知是“笔杆子”伏案工作的场所。
他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夫人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游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女儿胡木英曾经这样回忆父亲胡乔木: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的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
“秋深深未解悲秋”
在胡乔木家的客厅里,我听谷羽和木英叙述着胡乔木最后的那些日子……
胡乔木总是那么瘦削,那是长年累月在毛泽东身边,昼夜颠倒,工作又高度紧张,落了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过,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大病,所以步入晚年时,身体还算可以。1989年春夏之交,他和夫人谷羽还应邀赴美,双双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七十七岁的他尚能适应长途旅行和种种社交活动。
[page]从美国回来之后,胡乔木打算回老家江苏盐城看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思念着故乡,而故乡的朋友们也一次次邀请他回乡一游。
1990年5月,趁春暖花开,胡乔木携夫人谷羽离京南下,取道南京,准备返梓。在南京,忽地发现便血,不得不改变了行程。去南京的医院检查,大夫查明他的直肠里有硬块,主张马上动手术切除。他和夫人商量,并征求保健处的意见,决定还是回北京再检查一下。
就这样,胡乔木未圆故乡梦,不得不半途而返,打道回府。
在北京医院一检查,查明是肠息肉,即转三○一医院动了切除手术。手术做得不错。不过,大夫注意到,有癌症的征兆,嘱咐注意休息、观察。
胡乔木患前列腺肥大症。这本是老年男子常见病,他每年都要进行检查。9月,在例行的检查中,大夫发现他有前列腺肿块。大夫怀疑那是癌肿,举行了会诊。一个多月后,确诊那是癌症。
于是,胡乔木又进医院,在1991年1月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在用X光透视时,大夫发现他的耻骨上有斑,断定癌已转移。医嘱静养。
他无法静养。中国共产党的盛大节日——建党七十周年即将来临,由他提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正由一个写作组紧张地在北京玉泉山写作。他要过问、审定这本将向全党发行的重要史著。他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不能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好这些“修史”工作——因为像他这样起草过中共中央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深知中共党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
病中,他又帮助薄一波修改回忆录。因为薄一波也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把文章送去请胡乔木看一下,改一下,已成了“惯例”了。
很多人劝胡乔木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一直摇头。大抵他已自知余日不多,此时终于同意写回忆录。一个工作班子已建立起来了,他要不断地跟他们谈话。不过,他的回忆录,几乎不涉及他自己,他所回忆的是毛泽东走过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
虽说癌已转移,胡乔木贾其余勇,仍在紧张工作,度过了忙碌的1991年。
1992年初,胡乔木突然感到腿疼。经大夫检查,大腿小软骨骨折。大夫警告,他的骨质已很疏松,随时可能发生大的骨折,即使在家中也必须拄拐杖。这样,他成了“拄杖老人”。诚如一位哲人所言,人的一生倘若缩成1日,那么在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傍晚三条腿。胡乔木多了一条“腿”,自知已是“夕阳近黄昏”了。
服用治癌药剂后,胡乔木头晕、呕吐,药物的副作用折磨着他。听说上海华东医院有一种副作用轻、疗效不错的治癌药物,3月,他去了一趟上海。4月,当他从上海回来时,副作用明显减轻了。不过,癌症的阴影依然难以驱散。遵医嘱,胡乔木在家中坐上了轮椅,以防骨折。
虽说胡乔木自我感觉良好,但家人已从大夫那里知道他患病的实情,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在1992年6月1日,胡乔木八十寿辰那天,亲属们为他祝寿——他本人向来不作兴这类事。
那天,最使胡乔木高兴的是,人民出版社派人特地给他送来了“寿礼”——赶印出来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书中收入他1941年6月到1986年2月的政治评论一百一十四篇,共四十四万字。这些政治评论,当年大都是以《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如今头一回透露了作者是谁。胡乔木一辈子为这为那编文集,现在才出了自己的文集。文集共分三卷,胡乔木生前只见到这第一卷。抚摸着灰绿色皱纹纸封面的文集,胡乔木瘦削的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本文集也是他在病中编成的,耗费了不少精力——要查阅各种报刊,要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要标明毛泽东、刘少奇修改过的字句,要写序言。……那序言先写了一稿,不满意,又重新另写了一稿。
病中的他,已无诗兴。十年前,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曾写《有所思》一诗,回顾那崎岖的人生之路:
七十孜孜何所求,
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歌黄落,
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
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
弦急琴摧志亦酬。
……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八十大寿后的一个月,病情急剧加重了。
那是6月30日晚,胡乔木觉得右腿特别疼,不知什么原因。
翌日下午,三○一医院的骨科大夫上门,原本是为了向胡乔木家属讲授如何护理、防止骨折的一些主要事项,因为他们知道胡乔木的骨质已很疏松。听说腿疼,经大夫一检查,断定是骨折——这是癌症病理性骨折,虽说他并没有摔跤或受撞。随即入院拍X光片,证实大夫的判断完全正确。
从这一天起,胡乔木躺上了病床,再也没有下过病床。他一步步接近人生的终点——从拄拐杖、坐轮椅到卧床。
由于骨折,加剧了癌细胞扩散。
8月2日,他在病床上,给母校扬州中学亲笔写信:
扬州中学:
你们写信给吕骥同志,请他为校歌作曲,吕骥同志因忙于他事,要我转请当代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建议我将原题词稍加扩充,我已和他合作了一首,前已送上,后觉此歌仍不适于作校歌,故又补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仍请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又另作了一曲,并唱给我听了,我觉得此曲旋律优美,感情洋溢,表示满意。现将新的校歌词曲再寄上,请查收。收到后,望简复表示收到。傅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来信望对他致谢。
胡乔木8月2日
这里提及的校歌,原是为了庆祝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胡乔木为母校题词,题词以诗行形式写的,结果被扬州中学用作校歌歌词。
8月14日,胡乔木转往三○五医院治疗。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派人看望他,他想亲笔复信,勉强执笔,因笔迹太乱,只得作罢,托来人带口信去上海。
9月初,癌细胞扩散至肝、肺,胡乔木的呼吸变得困难了,讲话也很吃力。
他已无法坐起来写字。9月9日,他躺在病床上,把信纸夹在一块玻璃上,吃力地亲笔给扬州中学写信——这是他这枝“笔杆”平生的最后绝笔。
信的全文如下:
江苏省扬州中学:
8月28日来信并给傅庚辰同志信,9月5日收到。我在病床上得悉你们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学习新校歌的热潮,自然也加倍感到兴奋。你们对新校歌的评价虽然过高,但是全校师生如此热情却使我这个在校六年(1924-1927江苏八中,1927-1930江苏扬中)的老校友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我说在病床上写信和写作歌词,这是实情,但我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来此慰问之类,对此我决不接见。此事务请坚决彻底做到。
胡乔木9月9日
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
此信由于“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扬州中学收到时已是10月4日,胡乔木已不在人世。
由于呼吸日渐困难,护士给胡乔木戴上氧气面罩。
9月12日,三○五医院发出了胡乔木病危通知。他却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既未写遗嘱,也没有作临终嘱咐之类。他念念不忘的是改定他的诗集。
胡乔木喜欢写诗,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病中,他想修订再版此书,增加了一首诗,增加了附录,又口授后记,让秘书记录、整理。
9月21日,胡乔木嘱,把诗集增订稿送钱钟书审定——他和钱钟书有着颇深的友谊,诗集初版时便请钱钟书题写书名。
才一两天,钱钟书就看完增订稿,退回胡乔木。9月24日,女儿木英把改定的后记、附录念给胡乔木听。胡乔木细细听罢,这才说:“就这样吧!”说罢,如同了结一桩心事。
病中,他每日早上听新闻广播,听家人念报纸。每日必读报,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这时的他,运用氧气面罩都感到气闷,改用呼吸机帮助呼吸。
9月27日,他从新华社上海电讯中得知,25日是文坛耆宿巴金八十八岁生日,文艺界纷纷向巴老致贺。他也要向巴金致贺,虽说这已是“迟到”的贺电。他要亲笔写贺词,无奈手已颤抖,无法握管。于是,他只能轻声口授电文: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胡乔木。”他的生命列车,已经悄然驶入终点站。当天深夜十二时,血压剧降,接近零。
亲人们急急赶到医院,他已不省人事。大夫们尽力抢救,进行人工呼吸。翌日晨七时十六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曾写过《秋叶》,而他正是在叶落知秋的时节离开这个世界:
旋转,低回,依依地眷顾,
秋叶落下来,夹着些絮语;
在乡间人迹稀疏的去处,
随雨雪消融,化成了沃土。
在他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10月3日发出四千字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由于不再举行追悼会,这电讯实际上相当于悼词。电讯末段,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为才学超群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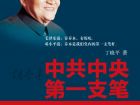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