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低潮"
摘要:"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说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钱正英:如果说"文革"前后是水利的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到80年代初期水利又进入一个低潮。
马国川:这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水利反而进入一个低潮了呢?
钱正英:"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说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年周总理讲,搞水利比上天还难,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是因为水利不但涉及自然环境,而且还涉及社会,解决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
马国川:改革开放后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一些人似乎也没有认识到水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生产关系,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没有化肥、水利、科技等生产力基础,粮食也不可能一夜迅速提高产量。
钱正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偏废。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通水旱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在主要江河上初步建成了防洪体系,并开始水资源的综合开发。据1988年的资料,全国的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的两亿多亩发展到七亿多亩,在不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的灌溉土地上,提供了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三分之二。中国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兴修水利的决策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马国川:但是在肃清"文革"期间"左"的流毒时,有人提出水利也是"左"的产物。
钱正英:1979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报纸上开展农业思想的讨论,其中对水利建设议论颇多,核心问题是对水利地位、作用和成绩的估价,认为水利投入很大,浪费很大,效益不好,这些不同的议论对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有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中央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研究,他在水利部一个很简陋的饭厅召开了水利建设问题讨论会,花了几天时间,认真回顾了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损失,形成了共识:水利一定要办,但办法一定要改。会议纪要上报了国务院,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扭转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水利的看法和评价。最后我们算是过了关。记得那个时候李先念因为腰疼住在北京医院,过了关以后我去看他,他住在医院里边还不太知道外边的情况呢。在那个报告里还引用了李先念的话来批评水利工作,当然是断章取义。我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还把你的话拉来批我呢。李先念腰疼躺在床上,一气坐起来了,说我李先念批你钱正英?
马国川:当时社会上以及政府内部,都对水利有怀疑的声音,个别中央领导人似乎也对水利有些看法。
钱正英:对,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反对修水利,认为是"左"的产物。80年代有几年,每年都要发"一号文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有一次他一个人给领导同志去汇报工作,回来后把一本笔记本给我,他说领导同志对水利说了很多反对的话,根本反对搞水利。杜润生感觉不好传达,这一传达水利部就没法工作了。所以他没开各部党书记会,先把笔记给了我。我翻开他的笔记一看,把水利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这样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了,最后我给陈云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陈云那时是中纪委书记,但他是经济工作的权威。我把笔记本送给他。几天以后,在一份中央文件上陈云加了几句话,说水利是很重要的。这才解了围。
马国川:在这种局面下做工作,压力很大,不容易。
钱正英:所以,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中央下划到各省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都挪到别的方面去了。看来,要使人家重视我们水利,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认识正确。建国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辩论,就是中国到底该不该搞水利?第一次是在"大跃进"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在"大跃进"中自己都搞糊涂了,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人家提出的种种责难,我们只能低头考虑怎么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来认识事物的规律,怎么把错误搞清楚、清理好,很难理直气壮地辩论。第二次辩论,在80年代初。这时我们心里是有底的。我们认为,虽然"文革"期间有很多"左"的东西,但在60年代初水利打了防疫针,而且是相当厉害的防疫针。广大干部、很多同志都知道这些事情,对水利应当如何搞心里还是有底的。要人家重视水利,对我们自己来说,关键就是要认识正确,自己心里有底;相反,如果自己搞不清楚,领导个人吃苦头事小,广大群众由于我们的错误吃大苦头,那就非同小可。
马国川:这种清醒的认识很重要,也很难得。
钱正英:所以在拨乱反正后,水利部门做了这样的决策:水利一定要办,办法一定要改,要依法治水。1981年在全国水利管理会议上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巩固现有基础,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
由于人民公社对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起来,所以那时候搞的水利、小化肥等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等到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这些条件和被解放的生产关系一结合,就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可是到80年代中期,潜力充分发挥起来了,后劲也没有了。我记得1984年书记处开会讨论"一号文件"时,杜润生要我参加会议,讲一讲水利对农业的必要性。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耐心听我讲完后,就说了一句"我保证今年还是丰收"。那一年确实丰收了,但也是一个拐点,1985年后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徘徊在四亿吨左右,农业形势严峻。
马国川:水利又怎么样呢?
钱正英:水利面临两个危机: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马国川:难以为继了。
钱正英:各方面开始重新重视水利。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水法》,第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列入农村的中心工作。1988年我就从水利部转到政协工作了。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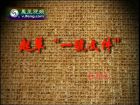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