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拨乱反正
摘要: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振兴中华,路在何方?这自然是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思考的头等大事。
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振兴中华,路在何方?这自然是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思考的头等大事。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国际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已发生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这是我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主持正义的其他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巨大胜利。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2月28日,中美双方经反复磋商,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方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原则立场,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联合公报》还规定双方将为逐步开展中美贸易以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领域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主题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发表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当晚,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田中角荣一行。《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他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双方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
毛泽东同志把握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我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1974年2月,他在接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也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高瞻远瞩,抓住契机,推动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他首先想到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教育。他自告奋勇抓科技,抓教育,主持召开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领导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果断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
科教的春天 当时,像枷锁一样紧箍在全国知识分子头上的是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这是指1971年8月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王震、邓力群同志谈话时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针对有人谈到“两个估计”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他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尊重教师。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写了一篇“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内参,刊登在《情况汇编》特刊上。内参分析了“两个估计”的出台背景,认为“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教育工作者积极性,是教育工作的障碍,必须彻底否定。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示。
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质,实际上否定了“两个估计”。随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不仅教育战线,其他战线也从中看到了希望。
1978年3月和4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两个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的著名论断,把千百万知识分子从“臭老九”的恶名中解放出来,成为受人尊敬的人。这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观点,改变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促进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郭沫若同志的讲话代表了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心声,随之,广大知识分子欢呼: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
我经历过教育寒冬的严酷,也感受过教育春天的一派生机。20世纪70年代,我在鄂西北山沟里参加筹建第二汽车制造厂时,正赶上高校停办,懂管理懂技术的人才紧缺,原有的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背负着“臭老九”的压力,搞得灰头土脸,难以发挥作用,一度使建厂工作走了许多弯路。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狠抓整顿,二汽建厂走上正轨,但需要的大学生还是没有来源。所幸当时厂里有大量文化基础较好的“老三届”中学生,于是二汽与华中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办职工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在二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成为技术和管理骨干,有的现在成了二汽的主要领导成员。参加一汽和二汽建设的实践,使我对邓小平同志重视科技教育的思想由衷地拥护,在我心中打上了永恒的烙印。
恢复高考 说起恢复高考,千百万人都会感慨万千。当时,“文革”造成的人才匮乏、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大制约。在这一情况下,教育怎么搞,大学怎样办,人才怎么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被废止的。1966年至1969年,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
1970年,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高等学校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招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调查,学员入学前,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这些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的学员在同一教室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还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展全面整顿,他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发表意见。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同志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找人,确定了一个包括吴文俊、马大猷、唐敖庆、杨石先、苏步青、查全性等专家学者的33人与会者名单。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专家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有的专家指出:高校招生实行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有的专家提出了恢复高考方案,即“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要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立即恢复高考,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
此时,教育部已经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招生工作总的原则依然沿袭“文革”中确定的16字方针。8月4日,教育部的《意见》报送国务院。
8月6日,针对与会者在座谈会上建议尽快改变用推荐的办法招生时,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并强调:“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改成‘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他还在会上强调要加强科技和教育的管理,表示: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邓小平同志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座谈会总结讲话中宣布:“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会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1978年2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中央领导同志均圈阅同意。
9月19日,针对教育部对高校录取的政治条件依然规定了许多“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同志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最后形成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这基本上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了全社会强烈反响。过去,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这一改变使无数青年才俊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走进了大学校门。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促进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纠正“左”的错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0月3日,邓小平同志将教育部修改后报送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批送华国锋同志:“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同志很快批示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0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部再次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招生政策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喜讯一经公布,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青春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大龄青年们,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开始了彻夜苦读。当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人。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印刷试卷!最后,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及时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恢复高考的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扩招。
1977年12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杨峻等6位教师写信给邓小平同志。信中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当年有1.7万多人报考,考生中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招考所不可比拟的。但该院招考的28个专业总计招生135名,仅占报考人数的0.8%,而经过初试、复试,留下的400余名考生的业务水平都是比较好的,就连初试被刷掉的许多考生的水平,也有些超过当时该学院的在校学生,可是由于名额太少,不但他们早已被刷掉,而且已通过复试的400人中的许多人,也不可能被录取。音乐专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是不容易的。像今年这样众多的音乐人才的涌现,真是难得啊!他们年轻,有很好的音乐素质,应该对他们及时培养。对这些有才能的青少年来讲,不能被录取,无疑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很可能再也没有学习音乐的机会或失去继续学音乐的信心而改行,这对今后音乐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建议:能否不受名额限制,将确有培养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学标准的青少年留下入学,以便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
仅仅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在12月11日作出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结果,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实际录取新生213名。在邓小平同志关心支持下,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才得以展开,一大批富有艺术才华的音乐学子实现了他们的求学梦想。
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不仅给国家的振兴带来希望,也给渴望学习求知的无数青年带来希望,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一时很难满足广大青年的升学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到浙江温州出差,乘汽车途中,留宿雁荡山。次日清晨,我外出散步,看见三个小尼姑正在用功晨读。我好奇地问她们读的是什么经书,她们笑着给我看所读之书,原来是高三的语文课本。我问道:“庙庵中也学文化课吗?”她们回答说:“不是。我们今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因此出家为‘尼’,在这里复习功课,准备明年再考。”听了她们的话,我特别理解她们求学的迫切心情。联想到“千岛湖惨案”,也是高考落榜生所为,同样给我心灵巨大震撼。我想,将来国家经济发展了,能让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于国于民皆是一大幸事。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大学本专科的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3万扩大到2007年约570万,高考录取率由4.8%上升到56%,为广大青年铺就了一条成才之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平反冤假错案 这一时期,全国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这成为当时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同志与前来看望他的胡耀邦同志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当时,胡耀邦同志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为90多名右派平了反。12月10日,中央决定胡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支持下,他一到任就坚定地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随后的几年中,按照党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共同努力,全国60多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直接参与,至1982年底这项工作才基本结束。全国共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多名错划的右派得到了平反。一大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重返工作岗位,解放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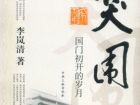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