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搞建设,经济走进死胡同
摘要: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急剧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量。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经济恢复,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76年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为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城镇职工工资不但十几年没有上调,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从绝对值来说,1976年(GDP为4704亿元)全国人民工作365天只相当于2007年(GDP为24.7万亿元)工作1周的GDP。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1/3。1976年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5.8亿美元。
以上这些数字,固然已足以在宏观上描绘当时的经济困境,但还不能具体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特别是对青年人更是如此。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时的情景难以忘却。首先,由于物资的短缺,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行限量供应。生产资料是实行计划分配,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则是凭票证限量购买,各种供应票证达六七十种之多。
吃饭要粮票 粮票对青年人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可是,对我们这些用过几十年粮票的人来说,都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为什么会出现粮票?还得从解放初期说起。那时我在上海念书。当时国民党刚从大陆溃逃台湾,但反攻大陆之心不死,从军事上、经济上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手段,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破坏,并妄言“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治理不了上海,不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他们所用各种破坏手段中重要的一种,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与奸商勾结破坏粮食供应。记得当时由于奸商大量收购囤积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粮食,不但使居民购粮十分困难,而且粮价飞涨。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打击奸商,另一方面从各地向上海紧急调粮投放市场,使囤积粮食的奸商顶不住了,不得不跟进抛售。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使我们有了从长计议的时间。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急剧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量。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1955年又制定实施了《市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作为此项政策的配套措施,于同年11月正式印制使用。粮票种类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只有全国粮票可在全国范围通用。
粮票的使用,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对保证居民的口粮供应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在“文革”中,粮食配给本来就比较紧张,又动员大家“主动”要求减少配给数量,人们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例如,对不同职业和岗位的人群,要核定不同定量标准和各种粮食的比例,男性女性还有差别。粮票以地方为主,只能在当地指定的粮店凭户口本发放,如果要到外地出差,还要由单位开介绍信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定期使用,过期作废,而全国粮票无时间限制,因此居民都想方设法把节省的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加以保存。这样全国粮票无形中就变成一种“有价证券”,记得当时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鸡蛋,几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塑料盆等等。
有一位外国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就同我讲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由于他喜爱中国文化,课余时间就骑自行车外出请人教他书法。有一次,下课时天色已晚,饥肠辘辘,他骑车回校途经东单,看到一家饭馆,想买几个包子充饥。当他拿出钱要买时,服务员向他要粮票。他说:我是外国人,没有粮票。服务员说,外国人也要粮票。这位外国朋友会说中国话,还继续同他理论说:前几天我在另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就没有向我要粮票。岂知这位服务员很讲原则,用现在的词汇可以叫做坚持“国民待遇”,对他说,他们要不要我管不着,我们这里就是要粮票。正好当时旁边有另一位买包子的人看到他们在“讨价还价”,就慷慨地拿出几两粮票送给他,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据这位朋友说,因为他未见过粮票,感到很新鲜,当时他没有舍得用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呢。他还说,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了,他仍记得那是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可惜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否则真应设法感谢他一番呢。他的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当时实在不足为奇,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的确还不失为一件难忘的趣事。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粮食大幅增产,特别是农产品经营和购销体制的改革,粮食凭票限量供应的制度才取消,粮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食品凭票证限量供应的还不只是粮食,食用油、肉、鸡蛋、煤等也是凭票、凭本供应。新鲜鱼在北京市场基本上看不到,咸带鱼只能碰运气才能买到。每当快到冬季,街道就组织居民限量购买过冬储存的大白菜等等。不少日用品如肥皂等也凭票证限量供应。
穿衣要布票 说到穿衣,当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布票,每人配给的数量很少,只有结婚、丧葬才能一次性地增加一点供应量。因此,当时连面粉袋、进口化肥的化纤布袋都拼缝起来做被里使用。布料的花色也很单调,无非是草绿色(军服)、蓝色、灰色、黑色,春秋季能做一件浅灰的布料中山装就觉得挺神气了。“文革”刚结束时妇女开始穿花衬衫,所谓花衬衫,实际上不过是在白布上印一些红、黄、蓝、咖啡色的小圆点而已。那时,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出国的机会很少,出国的服装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动的单位,集体做几套服装,像道具一样,谁出国或有外事活动就谁穿,回来后立即归还。对穿衣来说还不只是衣料限量问题。由于当时成衣的尺码档次很少,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因此除了自己缝制外,主要靠到裁缝店去做。当然,衣服打个补丁,补个袜子,缝个被子等都得自己动手,这是大家必须学会的“基本功”。但那时到裁缝店做衣服也并非易事,我就有过这样一段遭遇。
三级服装加工部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买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衣,在北京一连跑了七家商店,竟然买不到一件合适的。我的夫人建议说:“别再跑了,还是买块料子找个裁缝店去做吧。”于是我们买了一块仿绸料子,去找个地方做。谁知从西单找到甘家口,都说他们做不了。原因是说我是特殊体型,他们只能做标准体型的。这使我非常纳闷,我真不知道自己的体型“特”在哪里。想来想去无非稍微胖一些,可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胖得并不过分。这时真感到非常无奈,衣服买也买不到,做也做不了,总不能光膀子吧。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继续“奋斗”,锲而不舍地再去找。到了四道口,终于找到一家说可以做的裁缝店,当时真有点喜出望外。裁缝师傅为我量好了尺寸,把尺寸单的副页夹在料子里,算是手续办理完毕。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来取?回答说11月。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做这么一件衣服怎么会要大半年的时间呢?便同他商量说:“您看,我这衣服是夏天要穿的,11月才能拿,都到冬天了,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赶一赶。”他很干脆地说“不行。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接的活儿都快要堆到屋顶了,怎么做得过来呀?”我一看,他说的也确是实话,便向他建议说:“既然活儿这么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呢?”“多找几个人,您说得倒轻巧,您是劳动局长吗?”经他这么一说,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劳动指标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当然也就彻底失望了,只好要回衣料继续去碰运气。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到了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市场的西北门口有一家绸缎店,便信步走进去随便看看。忽然发现店内挂了一个可以做衣服的横幅,心里高兴地想,终于又找到一家,便问他们像我这样的体型的衣服能不能做,答复说可以,但同时营业员指着那横幅,让我看一看。我抬头仔细一看,那红布上粘的白纸剪的字是:“三级服装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便请他解释一下。回答说:“‘三级服装加工部’的意思,就是加工技术水平低,也就是说做坏了不赔。”这种“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然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还是硬着头皮问了他一句:“你们总不会故意给做坏了吧?”他的回答是:“当然不会。”这倒也给我增添了几分信心,于是量好尺寸,办好手续,取衣的时间也还算说得过去。总算带着“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高兴地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约定的取衣时间到了,先后去取了两次,都说还没有做好。按照第三次约定的时间又去取衣。记得那天还下着雨,是打着伞去取的。我问他们做好没有?查了一下说做好了,便取出让我试一下。我一看,口袋、袖口和下摆缝的线全都是波浪形的,再一试更糟糕,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同他们理论起来。我说:“你们看看,这衣服怎么穿呀?再说你们缝的‘波浪线’如果在衣服里面倒也算了,全在外面缝得这样弯弯曲曲的,多难看呀!”谁知他们不但无一点歉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就告诉您,这里是‘三级服装加工部’,做坏了不赔,您硬要在我们这里做,现在又埋怨我们做坏了。”听了他们这番话,我自知“理亏”,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并非硬要在他们这个“三级服装加工部”做衣服,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再也无言可对,只好拿着这件实在不能穿的衣服,颓然走出这家“三级服装加工部”。
我讲的这是一个发生在30年前亲身经历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也许有些青年人根本听不懂。的确,不要说青年人,就是我自己现在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可这的确是曾经发生过并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房子越住越小 说到住房,更是不堪回首。回想解放初期,我大学毕业到长春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虽然当时条件很苦,天气又冷,但是我们党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干部政策,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无比温暖,大家积极性很高,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在建设工厂的同时,一栋一栋的职工宿舍拔地而起,在大小不一的单元公寓房中不仅有厨房、厕所,有热水、淋浴,还有木质地板。开始我们都不敢想象这是为职工们建的。然而,当我24岁结婚时,厂里就分配给我们一套这样的两居室单元房。像江泽民同志当时是处级干部(当时一汽的干部比地方高半级,他享受地市级待遇),住的条件就更好了,是大屋顶的公寓楼。这样的住房条件,使我们内心深处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不过好景不长,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调离一汽后,到80年代初,不但居住条件每况愈下,还住过“干打垒”、农村的“简易房”、“筒子楼”、“办公室”等等。我相信我的居住情况当时还不算是最差的,有不少职工结婚多年仍长期住单身宿舍,很多年连“筒子楼”都住不上的也大有人在。据统计,197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居然低于1952年的人均4.5平方米的水平,可见当年的住房问题是多么严重。改革开放30年,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07年底,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8平方米。
出行难 说到行,当时出门不叫乘车,叫挤车,挤公共汽车,挤火车。我乘过最挤的火车,站着的人挤人,连空隙都没有。我的夫人为挤公共汽车被人挤倒,还摔断过骨头。路不太远自然是骑自行车,平时骑车还好,冬天也是怪冷的,所以白纱布缝制的大口罩就成为必备品。骑自行车也并非没有危险,特别是路灯昏暗的地方,不小心也会出乱子。有一次晚间我骑车经过一条小街,一不小心碰上了一个半开的下水道井盖,摔得我人仰马翻,幸好还未伤筋动骨。后来,我设法弄到一张自行车票,花了180元买了一辆带磨电灯的永久牌自行车。但骑了没有多久,可能因为这辆车太有诱惑力,竟被小偷偷走了,让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当时我国的汽车很少,卡车主要是一汽生产,二汽刚投产不久,产量还不大。由于卡车长期严重供不应求,而一汽每年获得的利润,基本上都上缴国家用于其他项目的建设,工厂本身难以进行产品更新和扩大再生产,在这种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各地不得不自己仿造“解放”牌卡车。当然,他们不用“解放”牌而换上了自己的“品牌”。由于投资和技术有限,产量、质量和效益自然很差。1978年第一机械工业部让我负责调查全国汽车工业的状况,以便制定整顿和发展汽车工业的规划。在调查中,我发现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区、市都有所谓的“汽车制造厂”。各地办的汽车厂,生产规模小的年产只有几十辆,一般也就几百辆、千把辆,而实际上多数是外购一些包括残次品在内的零部件拼装的。这种“小、散、乱、差”的状况,不但给国家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生产出的汽车基本上也是不合格的,污染环境,也很不安全。有一件事让人觉得特别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种车子看起来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勇往直前。”我话音刚落,同行的同志就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们生产的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不能往后退。”当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拖拉机极少在田间作业,而是在公路上跑运输,效率更低,安全性更差,污染更大,使用成本更高,是对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轿车产量更少,主要是上海牌轿车和北京吉普。当时,我国的汽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国外汽车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再加上当时“汽车厂”林立,无序发展,对能源和资源也造成很大浪费。现在我国汽车工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取得惊人发展,虽然随之也带来了一些能源、交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但这是发展进步中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也是寻求新的科技和政策、法规可以解决的问题。
理发的烦恼 理发,比起衣食住行来虽还算不上大事,但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在那个时代,凡是中年人大都有过理发烦恼的经历,主要是每次理发都要排队等待很长时间。20世纪70年代,我在工厂里当领导,当时办工厂就是办社会,特别是在偏僻的山沟里更是如此。办社会当然也少不了要办理发室。包括我在内的职工们,对那时的理发室意见可不小,不但排队等待的时间很长,而且理发时浪费的时间也很长。如果听说厂里给职工弄来什么难买到的鱼、肉、菜等,或自己有什么事,理发员竟会丢下理了一半头的职工,跑出去办自己的事。弄得去理发的职工无可奈何,怨声载道。后来我看这样下去实在不像话,想了一个“月评月奖”的办法,每月开一次评奖会,大家来个自报公议,评上先进的理发员发给奖金。希望通过奖励先进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谁知事与愿违,每次评奖时,大家是“当仁不让”,谁也不甘“落后”,有时甚至还争得面红耳赤,把“月评月奖”弄成“越评越僵”,难以为继。可奖金一发,要取消就难了,最后只好把奖金平均分配给大家了事,而理发排队的情况却依然如故,职工对理发的牢骚也丝毫未减。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理发员的工资按理发的数量来计算。这个办法一实行,立刻见效,排队等待的现象大大减少了,理发员的效率也空前提高。可是,出现了“高速切削”式的理发,使理发质量也空前下降。有的职工到我这里来“告状”时,不待他申诉,我一看他的头发被推成一个“锅盖头”,就已经又好气又好笑。后来又不得不给理发员规定每天理发的上限,即一天理发最多不能超过几个人,超过限额的不计工资,目的是想遏制他们“高速切削”。然而这个办法仍不见效,他们还是“高速切削”,“切”完后,提前收工。我讲的这种现象,固然有当时“文革”干扰的因素,那时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这种类似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调来北京工作,星期日去理发店理发,往往连排队带理发,差不多也得花上近半天的时间。其实我理发最简单,从来不要他们给刮胡须,也不吹风,理发本身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虽然自己不能给自己理发,我还是下决心买了一把理发推子,有时对着镜子把自己两边的鬓发推一推,以延长理发的周期,节省一点排队的时间,更主要是学着给孩子理发,免得孩子再花时间去排队。因此,那时我总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有哪一天不要再排队等待理发就好了。
我讲的是理发的烦恼,但这只是当时短缺经济和“大锅饭”体制在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些长期普遍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干部无能吗?是理发员不好吗?都不是。也许有人会说,那时我们那里的理发员就不像你说的那样,服务态度很好,还是劳动模范呢。当然,各行各业都有劳动模范,我们也应当以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事迹为榜样,要求大家向他们学习。而我们过去却总是认为,人人都应当也可以成为和劳动模范一样的人,思想政治工作是万能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问题并不重要。而实践证明,凡是带普遍性的问题,就必须从体制和管理制度上找原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去那种理发的烦恼,改革开放以后已悄然消失,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变了,服务业放开,不再吃“大锅饭”,“铁饭碗”也没有了,大家要靠服务态度、质量和效率去竞争,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甚至才能保住“饭碗”。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时髦”的代价 当时的日用品也极为匮乏,我曾经特别注意过儿童玩具,好像在商店里主要只见过赛璐珞的洋娃娃,铁皮做的玩具小汽车,充气的气球和塑料鹅、鸭等。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手表虽然还不属于奢侈品,但要想买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弄到一张手表票。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修了再用,一用就是20多年。由于误差已“超标”,且外表已呈老态,本想更新一下。可一是怕弄手表票麻烦,二是仅有的几种国产手表样子大同小异,也就懒得换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生产了一种“双菱”牌手表,造型稍有新意,价格虽比老式手表要贵一倍,每块130元,但无需手表票,于是就买了一块。可时隔不久,看到商店里又出现一种电子表,没有表针,是液晶数字显示的,不但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月和星期。觉得挺新奇,而且每块只要70元,于是当即就买了一块。当时我想,把这块刚买的“双菱”表拿到寄售商店处理掉,还能回收几十元呢。于是就直接向王府井一家寄售商店走去。当我把手表和购表的发票给营业员看了以后,他问我是寄售还是要他们收购。我便问他寄售和收购有何区别?他说,寄售80元,收购60元。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指着发票对他说:你看,我是130元买的,用了还不到3个月呢。他说:“您讲的全对,可您不了解,‘双菱’在手表厂内部销售给职工,每块只卖70元,价格定高了,谁买?”经他一说,我全明白了,只好成交了这笔赔本买卖。可是赶“时髦”的代价尚未到此为止。买的那块电子表起初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可是不到半年,就“未老先衰”了,显示器越来越模糊不清,表壳的电镀层也跟着脱落。我记得还不到8个月就完全报废了。由于手表引起的这番经历,1983年我到天津工作时,知道天津有个大的手表厂,于是就促使我关注怎样能把手表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给改一改?便带着这个问题到手表厂去调研。经过了解,发现这个问题固然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更多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国外专业化分工很细,有的厂专门做表芯,有的专门做表壳,有的专门做表针和表盘,而且工艺设备先进,效率高,品种多,变化快。他们所谓的手表厂,主要是造型设计,装配,出品牌,销售。而我国的手表厂则是“大而全”,什么都干,再加工艺设备落后等等,人家一个厂一年出300多种款式的手表,我们三年出不了一种新表。然而,这些问题还比较好办,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最不好解决的是体制、政策和管理问题。例如,我到天津手表厂去调研时,发现手表生产原来是个“暴利”行业,手表的成本每块只有8元左右,而售价要卖几十元。这么大的利润,为什么工厂还没有积极性呢?原来所获利润绝大部分都上交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与工厂和职工关系不大。还有更不合理的是,由于手表是“暴利”行业,当时各地纷纷上手表厂,顿时五花八门各种品牌的手表在市场上纷纷出现,价格都比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厂的便宜。小厂低价销售,这些大厂能不能也降价销售呢?不行。因为这些大厂的价格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范围的,自己无权调节。这一下可坏了,地方小厂的低价手表占领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厂生产的手表越来越积压滞销,陷于大幅减产、停产的困境。因此,这种管大放小的办法,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弄不好就成了以小压大,以小吃大,“蚂蚁啃骨头”,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些看来似乎是可笑的怪现象,当时正是困扰我们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改革,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这样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彻底改变我国手表工业的落后局面。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很大压力,毗邻香港的广东出现“逃港潮”。1978年广东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7.4元,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已达1.3万港元,差距上百倍。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从1951年封锁边境到1980年建特区前,外逃香港青壮年约7万人,撂荒耕地9万多亩,成为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述这些,也不过是30年前的真实情况,却好像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有些青年人听起来也许无法想象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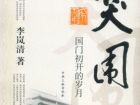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