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摘要: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过了合适时机,但他认为,重启改革机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不同意孙立平的判断。俞可平在2006年3曰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谈话说:“有人指出,目前我们对改革已经缺乏基本的共识,20多年前那种对改革的高度共识已经不复存在。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对改革的争论和分歧,表明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但它并不表示社会对改革已经失去基本共识。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共识的问题。共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共识是指多数人普遍类似的态度,它并不排斥少数人的不同态度。我们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共识政治’,就是指它遵循‘尊重多数,保护少数’的基本原则,即民主政治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但它并不排斥并且包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理解目前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各种态度,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我们对改革有着基本的共识。”
俞可平认为,下面几个判断是多数人对改革的基本共识:1、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即使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但与改革前的境况相比,他们的利益总量从绝对值上讲也是明显增加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2、改革不可逆转,这是改革的深刻性所在。3、改革的瓶颈已经位移,集中到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不同意孙立平的判断。孙立平提出“破裂”说之后整整一年,2007年11月,竹立家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的采访时说,在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背后,新的发展共识正在形成,其基本内容是“民主、民生、公正、和谐”。
关于民主。竹立家提出县一级政权要搞民主选举,再有就是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直选,以及政府行政要“公开透明”,建立公共财政等等。
关于民生。他说,社会各界认为,政府应该“有效地”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福利保障等“公共物品”。
关于公正。他说,政府处于各种利益关系的中心,最重要的是遵循社会公正原则。“应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不管穷人富人,其基本权利应当得到一视同仁的保护。
关于和谐。竹立家指出,和谐的核心是利益公平分配,民主和公正是和谐社会的“两个最根本的制度支柱”。
竹立家提出的“新共识”,没见什么人反对。实际上,“竹四条”的内容已经散见于大量媒体议论,但把它们归纳起来系统地概括为“新共识”,竹立家是第一个。竹教授很谦虚,他用“试图”两个字解释自己的努力:“新发展共识是试图对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价值坐标。”
竹立家提出的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确实抓住了新的改革攻坚的要点,是对改革面临的挑战的一种回应。
还有比孙立平更加激进的人士说,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了。改革当然没有死。如果说,1215年的《大宪章》为英国政治改革奠了基,那么请问,英国的政治改革持续了多少年?其中又经过了多少次“断裂”?
或许可以说,“断裂”是“阶段性”的一种表达和概括方式,意味着改革来到了新阶段的门槛。“断裂”,是排浪中的漩涡,是发展的“试错”环节,也是新的中国在分娩中遇到的阵痛。它传导出来的张力,不但表现为反思与批判,而且还蕴含着深深的希望,以便重新凝聚再出发。2008年,全国无以计数的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就是重新凝聚的檄文么?
有的学者对孙立平的“断裂”说表示担心。你总强调“破裂”、“断裂”,难免会使一部分人丧失对改革的信心,甚至唾弃改革,从而加剧民粹主义的情绪。提出这种担心的就有吴敬琏教授。
不过,吴敬琏也说,近来孙立平有所调整。在2007年出版的《守卫底线》这本书中,孙立平开始把“断裂”的两边缝接起来,希望尽快“形成改革的新共识”。他说:“改革要有公正的目标,要有民众的参与,这都是在反思中正在形成的共识”,这些新共识正在“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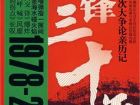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