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
摘要:何清涟最近在海外发表文章说,“陈卖光”卖了诸城的企业之后,卷款逃跑,人间蒸发了。这篇题为《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的文章是这样说的:“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陈卖光’因此...
何清涟最近在海外发表文章说,“陈卖光”卖了诸城的企业之后,卷款逃跑,人间蒸发了。
这篇题为《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的文章是这样说的:“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冬季号)
这当然不是事实。陈光完成了诸城(县级市)的企业改制之后,被提拔为山东菏泽市(地级市)市长,后又升任荷泽市委书记。在菏泽市长任上,陈光曾和我书信来往讨论改革,这些信一直留在我的手边。
“国企改革‘第一官’”,这是《南方周末》2003年10月报道陈光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其实,在诸城企业改制的同时,南方也先后进行了企业改制,只是诸城改制的响动格外大。
原因何在?一是诸城市的改制规模大。二是这件事发生在山东。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山东人。山东人朴直、讲义气,在全国口碑甚佳。但正如《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的一期报道所说,山东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官本位根深蒂固,私营经济发展落后。因此,陈光的改革在山东的争议格外大。
陈光原来是山东潍坊市团市委书记。1991年,35岁的陈光调任诸城市市长。诸城市是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陈光上任一摸底,凉了半截。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103家亏损。另外一些企业表面还说得过去,实际资不抵债。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80%以上,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达1.5亿元。陈光认为,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因此,“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
大规模变更国企产权,陈光堪称首例。十四大报告说,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要积极试点。这成了陈光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依据。
最初的试点,陈光选择了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当时市政府的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全厂职工提出全部买断。最后,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2万元,普通职工每人出6000元,把厂子买下来。这个国企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元电机有限公司。1992年12月28日,开元公司举行成立大会,诸城市工商局局长当场发执照,“企业性质”一栏出现一个新名词:“股份合作制”。陈光在会上说:“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这一年陈光撤消了5个企业主管局,人员一个不留,只保留一个经贸委。他说,政府越小越好,这是为企业改制扫除障碍。一些干部为此大哭大闹上访告状,但陈光不为所动。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陈光的改革确实有超前意识。
这一年他出任诸城市委书记,到1994年7月,全市288家乡镇以上的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这时,陈光被人起了个绰号——“陈卖光”。
陈光当市长的时候,诸城的改制由市长主导,当时的市委书记干了些什么?没人关心。陈光当书记的时候,这项工作又由书记主导,当时的市长干了些什么?也没人关心。这说明陈光是个强势官员。当然,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方方面面的矛头就都对着他来了。
1995年,两位学者来到诸城调研,写了一篇文章说诸城的改革是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在当时是很吓人的罪名,够抓起来的份了。该文发表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一家杂志上。
与此同时,1995年7月,山东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县一级企业改革会议。全省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来了,会议肯定了诸城改革模式。这一年,陈光当选为潍坊地委常委,成了山东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到诸城考察,诸城市体改革办一天最多接待过50个团体。这些考察团绝大多数都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带队,但他们回去之后并没有按照诸城的路子搞改革。
陈光成了争议焦点人物。北京一些“左”的杂志骂陈光是“私有化的先锋”、“败家子”、“歪曲党中央精神”、“复辟资本主义的带头羊”。有的文章指责陈光“违宪”,要求法办他。陈光每一个讲话,凡是外界能拿到的,都被人盯上了,拿着放大镜寻找字里行间的“罪状”。事情一直闹到2001年2月,北京的《中流》杂志还在批判陈光“毁灭社会主义”。这期《中流》发表署名“何仄”的文章说:“陈光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公然对抗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他竟以此为荣,自命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对于此类严重向中央挑战的言行不予严肃处理,党纪国法还有什么权威?岂不是要形成党将不党、国将不国的局面吗?”
一位原诸城市委机关干部对《南方周末》回忆说:“当时陈书记晚上都睡不着觉。”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陈光初衷不改。
诸城卖光的结果怎样呢?在企业中,原来无职无权的职代会变成了有职有权的股东会。1994年8月,有一项统计涉及诸城27家企业,其中24家原厂长经理被职工赶下台,变成了普通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30%还算少的。“现在是给自己干了!”一句话就消灭了懒汉。当然,股份过于分散也有弊端,由于企业分红高,两三年就可收回成本,职工的风险意识就淡了,对企业关注度降低。相对平均持股,也导致管理难度加大。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一线职工大量持股是最不经济的。对此,陈光引导企业“让经营者持大股”,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在这方面,四达公司先后对股权结构进行几次调整,持股比例一次次向董事会倾斜,最终达到《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要求,取得了好效果。
诸城卖光的代表作是诸城市农用车厂。当时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正想进入农用车行业,到山东寻找合作伙伴。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你们!”一家资产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引进北汽3000万元投资,上马生产福田牌农用汽车。三年之后,诸城市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不只500万元。这个小厂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农用车的巨无霸——北汽福田。
但是某些“理论家”是不看这些的。
陈光的改革除了在内地引起争议之外,还有一家香港报纸报道说,江青的故乡出了个陈卖光。事情闹到中央,中国人民银行派了12个人来查帐,没有呆账、坏账。1996年1月21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奉国务院之命,带着财政部、经贸委、审计总署等9个部委官员组成联合调查组来诸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深入企业与干部和工人座谈。陈光不免有些紧张。洪虎临走时说:“你们放心,我代表国务院来,是来总结改革经验和成果的,是来研究怎么发展的,不是来找事的。”陈光听后放了心。后来调查组到潍坊,宣布了调查结论: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又带着9各部委的官员、专家来诸城调查研究,其中有吴敬琏。
朱镕基要求把诸城全部企业名录拿来,他圈中哪个就调查哪个。那次调查力度很大,朱镕基在诸城没有讲话,但是他到了青岛之后表扬了诸城的企业改制。他说一开不相信诸城的“一股就灵”,这次亲自来看了,比较满意,觉得诸城有几点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同时,他也指出了诸城的几点不足。朱镕基得出的结论是,诸城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3月24日,跟随朱镕基考察的吴敬琏在山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诸城对272家小企业进行改革,采用多种形式放活小企业,在明晰产权和政企分离这两个重大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企业效益和全市财政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成绩喜人。吴敬琏还提醒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经营不要干涉过多。
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现在诸城经济发展快,没有失业问题,找工人要到外地去招。来诸城的人看到这里的道路宽阔整洁,高级轿车很多,富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都是周围县城没有的风景。诸城GDP连续多年年均增速20%,美国泰森、沃尔玛、日本住友、伊藤忠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在这里落户,诸城一跃进入中国百强县。
1997年6月,陈光调到山东荷泽地区行署,先任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
一位作家写到,陈光来荷泽报到那一天,上了黄河大堤,“他忽然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他对着黄河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他在荷泽继续进行改制探索。
荷泽是山东最穷的地方。陈光到菏泽这一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菏泽当时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就需要10亿元,菏泽干部的工资发不全,陈光的工资也立即从1000多元降到700多元。贫穷和愚昧结了婚,生出个孩子叫落后。这里“官本位”猖獗,办事拖拖拉拉,歧视外来投资,吃拿卡要盛行。干部们还挺骄傲:“别看我们不会抓工业,我们会种庄稼。”菏泽的职工穷得没钱买厂子的股份,怎么办?陈光就送。菏泽的穷困落后程度超出了陈光的想象,他觉得这些企业根本不会有人买,只有送给有实力的企业来救活,送给人家人家还不一定要。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卖掉企业,不如说是送出包袱,送出债务。说是送出去,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如果孩子能养好,换个爹娘又何妨?只要能把企业搞活,不管荷泽的企业姓荷不姓荷。”这使他又多了一个绰号——“陈送光”。
菏泽的工业极其薄弱,比起诸城来差了一大截,所以菏泽改制的结果不如诸城那么显著。
在这个时刻,我给陈光写信,支持他的改革。
1999年1月19日,陈光给我回信。当时电子邮件尚不流行,陈光写给我的信还是老派风格——中式红色竖格信纸,流畅的字体一行行竖写。
信中说:“不管你说的对与错,总会惹得许多人乱加指责。他们不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也不容人家分辨,只知道用的‘左’的大帽子压人。与其让他们大吵大闹,倒不如静观其变,过些时候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有这个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改革如大江东去,是什么力量也挡不住的。我对此充满信心。”
6月21日,他又给我来信说:“改革很难,民主不易,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灾难深重,真正与世界接轨,尚需时日。”这几句话沉甸甸的,是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改革者的箴言,既给人力量,又促人深思。所以,陈光这几句话,时常在我的脑子里回响。
2000年,荷泽撤县设市,陈光就任第一任市长。2002年,陈光被任命为市委书记。2003年,陈光下令市、县、乡三级都成立招商引资小组,一半干部在家主持工作,一半出去招商。有时陈光还亲自带队出去招商。而在诸城,引进资金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根本不管。
当然,陈光的改革并非百分之百成功,比如出售医院就出了问题。2004年,市政府借鉴江苏宿迁的经验,卖了5家医院。但菏泽的医院职工和卫生管理部门普遍反对,再加上有的购买者买下医院之后没有按照许诺进行投资,出现了诸多问题。2005年5月,市政府不得不把医院又全都收了回来。市政府发的文件说:医院改制的出发点是对的,在操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后来陈光说:“菏泽的医改情况很特殊,我不想多说。其实我不赞成荷泽医改,事业单位改革和企业不同。”
陈光仍然是老脾气,对各种纷至沓来的非议不予理会。他说:“我在改革时不会考虑这些,你处理我,把我免职我不管,历史会有定论。因搞改革被人骂,受批判,是正常的。关键是做人要有个标准,如果老考虑领导高兴不高兴,提不提拔,那就做不了改革者。”
陈光仍处于争议之中,荷泽就有一些人骂他。就在陈光推进改革的时刻,公安部门在荷泽一些地区查获了几起脱衣舞演出的非法行径。当地有人趁机说,陈光又多了一个绰号——“陈脱光”,陈光现在已经是“三光”了——卖光、送光和脱光。这“三光”的绰号,当然是一些人乱调侃。跳脱衣舞各处都有,该处罚谁处罚谁就是了,为什么单把“脱光”的帽子给陈光戴上?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陈光主政下的菏泽发生了巨变。2006年,全市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市财政收入猛增到30个亿。增幅全省第一,但总量还是末一位。菏泽的工厂有响动了,路变宽了,下水道不堵了,灯都亮了,绿化面积扩大了,公务员的工资涨上去了,黄河水也引来了。拿现在和1997年比,荷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90%降到12%。
2008年2月8日,陈光的一项政绩上了《人民日报》。菏泽2007年粮食产量491万吨,占全国粮食产量近1%,近5年新增粮食产量约占全国增产的5%。在农产品越来越紧缺、越来越金贵的今天,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菏泽春季的风沙和夏季干热风是威胁农作物的主要灾害。陈光上任之后连年大规模植树造林,终于建成完善的防护林体系,使风沙日数减少70%,年降雨量增加2.9%。陈光向《人民日报》记者宋光茂介绍说,荷泽农民因此每年增加收入两亿元。2008年初,在山东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将两辆农技推广车奖给了荷泽。
陈光说:“荷泽已经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俯仰无愧,改革者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政声人去后,无声胜有声!”陈光以巨大的勇气走出国企产权改革第一步,在竞争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从而给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他的实践,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脚印。
陈光对《新京报》记者说,他曾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官员仇和彻夜长谈,“谈得很深,农村改革、企业改革的深层次的东西。”他很欣赏仇和说的一句话:“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谁愿意做那些戳别人眼珠子的事情?”
2008年初夏,52岁的陈光调任山东省省长助理。按众人理解,虽是平级,当然更为重要,此后他的工作将覆盖全省。他的新任务是协助省长在全省开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包括企业改革、乡镇改革等诸多内容。陈光有了更大的舞台。期盼陈光锐气不减,为山东改革做出更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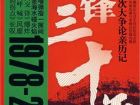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