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凌:首钢承包试验
摘要:1982年初,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给赵紫阳总理写了一封信,内容大体是说,在企业改革中,大型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物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这类企业不宜扩大自主权。小企业资金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自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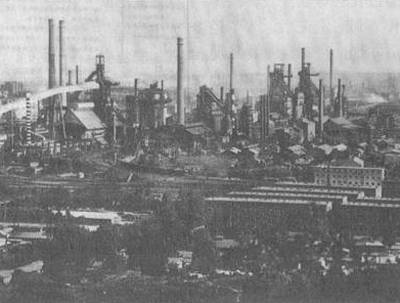 |
首都钢铁公司资料照片
承包制发生种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改革只在经营方式上做文章,而没有触及所有制
一封信引发的争论
我参与首钢承包制方案的设计要从一封信讲起。
1982年初,四川大学的一位老师给赵紫阳总理写了一封信,内容大体是说,在企业改革中,大型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资金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物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人的因素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这类企业不宜扩大自主权。小企业资金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自主权。
赵总理把这封信批给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研究中心是刚组织起来的机构,人大都是其他单位的研究人员,有问题就在一起开会讨论。根据赵总理的批示,暮桥就组织一些研究人员讨论这封信。我刚巧在北京,也参加了。
会上,多数人不赞成信上的观点,认为无论企业大小,技术水平高低,人在生产中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企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活动的余地和可以发挥的潜力就更大,给大企业以必要的自主权,使大企业有更大的活力,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蒋一苇和我都是不赞成信上的观点的,竭力主张在大企业搞扩大自主权,于是,我们商量,是不是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首钢试点?因为赵总理领导我们在四川搞扩大企业自主权已经近两年时间了,改革的对象有小企业、有大企业,有全民、有集体,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北京,首钢是大企业,是国家经委批准的八个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之一,很有积极性,而我又是解放时接管首钢的“老人”,做过工会负责人,对厂里的领导、工人都比较熟。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就从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四川省社科院各带了一个工作组,于1982年3月到了首钢,展开调查研究。
当时,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是周冠五。我们通过和周冠五及党委的成员交谈,到科室和车间细致调查,了解了很多情况。那时,首钢已在搞扩大自主权试点,虽然上边规定的试点条款并没有全面落实,但因为有了一定的生产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利润留成权、资金使用权、职工奖励权,在整体经济面临许多困难的条件下(当时正处在宏观经济调整时期),把首钢的经济搞活了。实行经济责任制后,生产经营的任务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责任感,同时,实行了有差别的奖励制度,打破了平均主义,提高了职工收入水平,职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退休的老工人告诉我,他们每天早晨的任务就是喊儿女起床,青年工人赶着上班,一边吃早点一边跑步的人有的是。
扩权三年的五笔账
根据扩权三年成绩,我们算了五笔账。
第一笔是上缴利润增加账。三年来,首钢的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上缴利润年均增长34.5%,上缴利润加税金年均增长27.91%,均创历史记录。
第二笔是利用企业留成的资金开展企业技术改造账。扩权前,国家一手向企业收交利润和税收,另一手向企业拨付基建和技术改造专款。扩权后,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用留成款进行重点项目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治理污染。扩权三年,企业留成占利润净额的11.6%,加上其他企业应提留的款项合计22063万元,其中的63.74%用于技术改造,取得很大成效。这是过去那种由政府拨款制度做不到的。
第三笔是生活福利账。由于企业有了留成资金,三年共为职工建设住宅25万平方米,占留成资金的15.4%,而这些钱过去是由国家单独拨付的。同时又用留成资金的6.12%支付了职工的医疗费、福利费、救济费等,而这些支出过去都是要计入成本的。从此,首钢建立了由企业留利支付职工社会福利费用的新制度。
第四笔是职工奖励账。过去,职工奖金是按政府规定的标准发放的。扩权三年间,首钢从实现利润中提取奖金,相当于上缴利润的3.01%,1980年实发奖金相当于3.99个月的平均工资,形成了奖金与实现利润挂钩的新机制。实现利润越多,职工奖金越高,但又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之内。
第五笔是市场调节账。1981年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整,钢材市场疲软,国家计划内的钢材许多分配不出去。由于有了产品销售权,首钢自销的产品占到总生产量的16.4%,企业经营向市场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五笔账一算,大家非常振奋。我们感到,扩大企业自主权把国家、企业、职工的权、责、利关系明确了,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分配也有了一定的比例界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行机制也发生变化了,新的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动力机制也形成了。企业的管理氛围焕然一新,职工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整个企业几乎换了一个样子。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探讨。大家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理顺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质上是合理分配劳动者创造的净资产(一般为上一年度)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净资产的分配是,一部分作为劳动力的价值(v)以工资形式发给职工,另一部分作为剩余价值(m)为资本家占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净资产(v+m)全部为劳动人民所有,再在国家、企业、劳动者之间分配。传统的国有企业的分配形式是,v部分仍以工资形式由企业分配给职工,m部分则以利润形式由企业上缴给国家。国家对集中起来的利润进行再分配时,企业和职工都是没有获得利润的权力的。实行扩大自主权改革后,企业可以从上缴利润中以利润留成形式提取一定比例,留给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与此同时,再从利润留成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工人的工资、奖励、福利等消费部分。这样,利润的分配在企业层面就改为由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进行分配了。
“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出台
这种分配形式比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首钢的同志感到,这种形式对他们这样有机构成高、管理基础强、生产潜力大的企业来说,激励作用还不够大,还不能保证国家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他们建议改为上缴利润逐年递增包干的办法,让这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酝酿提出的具体意见是:
第一,以1981年企业上缴利润指标为包干基数,每年递增5%,10年-15年不变,10年后,即1991年企业的上缴利润可由1981年的26810万元增加到43980万元,增长163%。如企业上缴利润递增小于5%,企业必须按规定缴足43980万元,如此,企业留利就会相应减少;如企业上缴利润递增大于5%,企业留利就会相应增加。这样,既可保证企业上缴利润的稳定增长,又可激励企业努力提高上缴利润递增率,取得一举两利的效果。
第二,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规定企业留利的使用方向和比例。经过讨论测算,首钢提出的方向和比例是:60%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20%用于集体福利,主要用于职工住宅建设;20%用于奖励和日常的福利费用。
第三,奖金与上缴利润递增率挂钩。如果上缴利润递增率达不到5%,职工奖金水平不变;如果连递增基数也达不到,则停发奖金;如达到或超过5%,每增2%可多发0.1个月的标准工资作为奖励。
第四,利用利润留成提取的奖励基金调整部分职工工资,实行内部工资制。具体办法是: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对确实达到上一级技术标准并圆满完成岗位责任的职工,由企业予以“升级”;如果第二年完不成任务,就取消升级;连续三年保持合格的,再把级定下来;调出首钢的不带所升工资。
以上办法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提升了一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上缴利润递增包干”。
实行这样一种改革涉及国家管理企业的一些根本制度,光靠企业是无法实施的,需要企业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同推进才能取得效果。于是,就以蒋一苇和我的名义向赵紫阳总理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批准在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由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给予支持。报告是经过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马洪转报的。报告很快得到赵总理批准,并指示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冶金工业部、北京市政府研究并组织实施。
对于这个报告提出的观点和具体办法,多数部门和同志是赞成的,但有的部门和同志并不赞成,后又经过几个月的讨论,才达成一致。上缴利润递增率由5%调整到7.2%,包干时间延长为15年。
首钢试点一展开,就采取了几条重大举措:一是在全厂范围开展制定责任制的活动,把包干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个岗位,形成一套规范的岗位责任制度:二是制定全厂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规划,分步实施,为不断提高生产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三是在职工中开展工资升级活动,提高职工的技术和收入水平。这些举措直接涉及职工的长远和切身利益,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生产水平节节上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要求学习首钢经验,实行上缴利润增长包干制。国家经委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适时选择了二汽、佳木斯造纸厂等六户大企业在全国试点,更多的企业则学习推广首钢责任制的经验。
当时,赵总理把首钢经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中说:怎样搞好一个企业呢?办法就是“政策+周冠五”,一个好的政策加一个好的企业家。
承包制得失
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发展到1984年,全国已有30多户企业实行。1984年春,我和蒋一苇又联合在首钢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总结试点经验,同时,与国家经委合作,提出了100个大企业的名单准备推广。同年4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和蒋一苇应邀参加,会议请首钢负责人介绍了经验。但会议开到中间,忽然传出一种说法,说首钢经验是否继续推广,还要研究。过了一天,就接到赵总理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参会的人有薄一波、田纪云、周太和(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池海滨(财政部副部长)、蒋一苇、林凌,还有其他几位同志。
会议主要讨论要不要继续推广首钢经验,下一步改革搞什么?是不是搞第二步“利改税”?参加会议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进一步推广首钢经验,另一种主张是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主要分歧点是首钢的做法会不会导致国有制变成企业所有制。会上,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当时首钢的企业留利比例计算,12年之后,首钢就会由国有制变成企业所有制。他们据此认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是破坏国有制的,不能搞。我们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感到,如果这个算法是正确的,那恰好证明“首钢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这个改革多么有效!至于说这个改革会不会改变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我们发言说,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国家与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方式和资金的使用方式,过去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和职工住宅建设,资金都由国家出,现在改由企业留利出,而且投资效率高,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仍然是国有资产,怎么可以说变成企业所有制了呢?在当时的气氛下,这种讨论显然是得不出结论的,因而,在多数人的坚持下,决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首钢、二汽等七户大企业的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继续试行。
然而,不同意见的争论仍在继续。首钢进一步提出“承包为本”,有的学者写文章还喊出“承包万岁!”对承包制的批评则仍然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承包制一度遭到冷落。1987年,全国各地对八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反思和总结,许多人认为,实行承包经营的责任制是实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一种好形式。于是,经过国务院提倡,这个曾一度受到冷落的企业经营方式又兴盛起来,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半年多时间内,成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承包合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企业经营方式也得到推广。
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成千上万,在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子都采取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其他经营方式,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许多问题相继出现。最突出的是,不少企业承包者为了实现更多的利润,竟不提或少提折旧,推迟设备大修时间,把存量资产作为当年新增资产上缴,使国有资产受到很大损失。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说是改革只是在经营方式上做文章,而没有触及所有制。后来实行股份制,推行现代企业模式,才把这些问题纠正过来。
全国推行股份制后,我和蒋一苇曾拜访了周冠五,建议首钢改行股份制,周不同意,坚持把承包制搞到15年。应当承认,首钢的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制与全国面上搞的承包制是有许多不同的。首钢虽然发生过盲目扩张、盲目兼并、盲目投资铺新摊子、盲目增加人员等错误,但从没有发生上面那些问题,而且比较理想地实现了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目标。这一时期,全国钢产量由1978年的3178万吨提高到1994年的9261万吨,增长1.94倍;首钢的钢产量则由145万吨提高到823万吨,增长4.68倍。用企业留利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额为116.57亿元,年平均增长18.1%,全部成为国有资产。与此同时,还上缴国家税利336亿元。
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之时,一些人担心,这种改革会把国有资产变成企业资产,损害国家利益,甚至会导致私有化。首钢的实践证明,这些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首钢的做法比起国家直接投资来,效益要高得多。现在看来,那些观点有多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意识形态气味很浓的、争论不休的严肃题目。我主张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为首钢浓浓写上一笔,这不仅是为了赞誉首钢,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有了高度自主权的中国国有大企业也曾创造出喜人的业绩。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