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
摘要: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同推倒“两个估计” 相联系, 在出版界还进行了对“ 四人帮” 强加给分别于1932 、1936 和1935 年在上海创办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 的拨乱反正。出版界这一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拨乱反正是分三步走过来的:推倒“黑店论” , 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正确解决三店从业人员革命工龄问题, 为一大批革命出版工作者恢复名誉;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 使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出版单位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作用。
宋木文
来自《出版史料》2004年第4期
笔者特别说明:此文是我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版战线拨乱反正长文中的一部分。当我完成此稿时, 即. 2004年10月26日上午, 杨德炎同志电话告诉我, 资深编辑出版家、著名学者、韬奋出版奖荣誉奖获得者陈原同志因病于晨5时逝世, 享年八十七岁。我同陈原同志相识并深得他的教诲有三十多年了。对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出版界、学术界前辈的辞世, 我更为悲痛。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 每涉及陈原同志处, 都引起我对这位多年躺在医院病床上神志不清的兄长、良师和益友的思念。因此, 我也就极其自然地、实事求是地用较多的文字回顾了陈原同志批判“四人帮”炮制“三十年代黑店论”,把出版界拨乱反正引向深入作出的突出贡献;回顾了陈原同志为恢复三联书店革命历史地位、在人民出版社建立三联编辑部以及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副牌改变为独立建制的出版单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一些资料的引用, 只要是出于陈原同志, 我都加以注明。本文所写, 对陈原同志来说, 虽然仅仅是他对出版事业杰出贡献的点点滴滴, 却也促使我以单独发表此文来表达我对陈原同志的崇敬和思念之情。同时, 也借此机会向为中国出版事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三联老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 向正在继续发展三联事业的在职三联人表示良好的祝愿。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同推倒“两个估计”相联系, 在出版界还进行了对“四人帮”强加给分别于1932 、1936 和1935 年在上海创办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拨乱反正。出版界这一有现实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拨乱反正是分三步走过来的:推倒“黑店论” , 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正确解决三店从业人员革命工龄问题, 为一大批革命出版工作者恢复名誉;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建制, 使这家有着光荣传统的出版单位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三十年代黑店论”的批判
新中国的出版事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解放区以新华书店为主要代表,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为主要代表(1948 年5月受党中央指示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关于三家书店以及后来合并成立的三联书店的这种历史地位, 既为它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出版实践所证明, 也是党中央做出的正确结论。1949年7月18日, 《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之下, 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的读者, 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 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 如邹韬奋同志(已故)等, 做了很宝贵的工作。”“中央指示”又指出:“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就像1947年7月2日至7月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实现了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两支革命文艺大军会师一样, 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两支革命出版大军在新中国首都也实现了会师。在1949年10月3日至10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他所作的闭幕词中讲: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是为人民服务的出版机关。他特别指出:“人民的出版工作者,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 甚至不惜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是这种出版事业的榜样, 全国的优秀的出版工作者都将跟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
在“文化大革命”中, “四人帮”颠倒历史、混淆是非, 污蔑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为“三十年代黑店” , 并进行追查, 是其整个反党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1966年2月, 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 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 这条黑线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而且诬指三十年代文艺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渊源, 曾在三十年代领导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并在建国后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干部和知名人士无不遭到残酷斗争和迫害。出版界也被定为“从三十年代到建国以来贯彻着一条黑线” , 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追查“三十年代黑店”的活动。在上海和北京这种追查“黑店”、迫害三店革命干部的活动尤为猖狂。胡愈之、胡绳、钱俊瑞、黄洛峰、徐伯昕、林默涵、徐雪寒、姚溱、张仲实、王益、陈原、邵公文、仲秋元、沈粹缜等一大批三店老同志都遭到了批斗和迫害。甚至还要追查明确肯定“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的中共中央1949 年7月《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 可见其矛头所向决不仅限于三家书店。据黄洛峰①揭露“张春桥……1967年布置搞三联, 不仅上海, 北京也搞, 我被提审了许多次。在文化部我被十多人提审, 我闻出那个味道不是在搞我们这些人, 是要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周总理。”许觉民②揭露:“我被提审的次数不少, 叫我吃惊的是一次上海来人, 要我讲三联的性质, 我讲了如何历史地来看三联, 有不少青年就是看了三联的书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时有一个人叫我住口, 说:‘我来告诉你三联的作用。它披着左的、革命的外衣, 起了国民党所不能起的作用!’”③
综上所述, 在出版界批判“两个估计”、进行拨乱反正中, 应当把所谓“三十年代黑店”作为重要问题加以清理。1977 年下半年, 在王匡同志领导下由陈原同志主持的出版路线是非调研小组也曾议论过这个问题, 并反映在调研小组工作成果的《极“左”思潮在出版工作中的一些表现》一文中。这篇载于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编辑的《出版工作》1978 年第五期的调研文章就曾把“三十年代黑店”作为需要清理和批判的问题提出来:“原出版口的一位负责人, 竟然指使人写一份黑报告送给陈伯达, 说什么‘出版系统的领导干部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 不仅是一条黑线, 而且是连锅端过来的黑店’。”但主要是由于我来出版界不久, 对出版界“文革”中有关情况了解不多, 所以没有建议对“三十年代黑店”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和展开批判。我和调研小组的同志, 都很感谢和敬佩主持调研工作的三联书店老干部陈原同志, 因为他独自做了充分准备, 率先对“四人帮”炮制“三十年代黑店论”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批判, 在出版界打响了关于三联书店问题拨乱反正的第一仗。
1977年12月, 在王匡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 着重批判了“四人帮”强加给出版界的“两个估计”。前已提到,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 出版界“十七年黑线专政”源于三十年代, 而批判“两个估计” , 理所当然地要追究其所谓“源头”的“三十年代黑店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陈原同志作了《驳所谓“三十年代黑线论”》的大会发言, 使与会同志加深了对出版界黑线专政论的实质和危害的认识, 也把会议对“两个估计”的批判引向深入。我听后也深受教育。陈原同志以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为依据指出:三十年代我党领导下的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工作, 是毛主席1940年高度评价过的五四以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革命作用的白区进步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列举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关怀下三店在白区如何适应环境开展斗争, 并在必要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 使“根据地和白区两支革命的出版队伍, 在不同战场上, 互相呼应, 互相支持, 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 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陈原同志在讲到白区这支革命出版队伍的发展壮大, 也讲到他们遭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和镇压时, 引出邹韬奋病重时回忆过这样的斗争场面:
1939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先从西安生活书店分店“开刀” , 不但将店封闭, 经理及职员被捕, 而且将所有生财用具搬移一空, 形同劫掠。……自1939 年4月起至年底, 不到几个月, 由西安而天水, 而南郑, 而宜昌,而万县, 而沅陵, 而吉安, 而临川, 而南城, 而赣州, 而金华, 而丽水, 而立煌, 而福州, 而南平, 而曲江, 而梅县, 而兰州, 而衡阳, 而贵阳, 而桂林, 而成都, 而昆明等等50余处的生活书店分店负责人都遭受同样的苦难。负经理责任的高级干部被无辜逮捕的达40余人之多。④
陈原同志以下面的一段充满革命激情的话结束他的发言:“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三十年代革命出版事业, 不是什么‘黑店’, 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影响下, 在白区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机关, 不管它有过多少错误, 走过多少弯路, 它仍旧是波澜壮阔的白区革命文化新军的一个支队。‘四人帮’想把它打成‘黑店’ , 想不分青红皂白把三十年代出版事业全盘否定, 是决计办不到的。”
这是一篇声讨“四人帮”的革命檄文。今天重读仍然感受到它的力量之所在!
陈原同志把这篇声讨“四人帮”的发言收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陈原出版文集》时, 在文前加了对了解这篇文章很有帮助的“题解和思考”:
1977年5月, 中央调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 首要任务在拨乱反正, 当年召开全国出版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驳“四人帮”诬蔑三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是什么黑线统治的反动“黑店” , 为三家出版社以及三家出版社合并组成的三联书店恢复名誉的长篇发言。由于当时某些极“左”势力的阻挠, 发言未能公开发表。1978年初中央党校内部出版的《理论动态》刊登了这个发言的摘要, 胡耀邦同志阅后指示《人民日报》, 于1978年2月3日刊登全文。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陈原同志的文章, 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时, 人们的思想解放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从这段简短的“题解和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原同志作这篇发言的勇气、智慧及其重要性, 更可以体会到在胡耀邦同志支持下才得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在当时的文化出版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
陈原同志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上所作《驳所谓“三十年代黑线论”》的发言, 受到国家出版局党组的高度重视。在王匡、陈翰伯同志共同主持下,1978 年1 月14日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三联老同志专题座谈会, 进一步批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的谬论。经历“文革”劫难后三联老同志首次的集会, 其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意义。胡愈之、黄洛峰、华应申、许觉民等领导和参与三联工作的老同志的发言, 使与会者特别是我们这些非“三联人”进一步认识到三店及其后合并的“三联”在白色恐怖恶劣环境下宣传真理、发展文化、培养人才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有力地批驳了“三十年代黑店论”。胡愈之同志说, 所谓“黑线”之长, 就是长到三十年代, 由文艺界到出版界。周扬曾封我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佘太君”。“文革”中三十年代都被说成是封资修。我还被一个单位批斗了两次。毛主席对三十年代有很正确的估计, 就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那段话。这是估计三十年代文化工作、出版工作的标准。毛主席还讲到“五四”以后二十年, 到1939年, 包含三十年代, 是文化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 估计很高。“四人帮”要推翻, 是讲不过去的。黄洛峰、华应申、许觉民等同志的发言, 着重介绍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党的中央局关怀和领导三店的情况, 介绍了三店所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救国言论集》、《帝国主义论》、《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入门》、《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歌曲集》等书籍对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的重大影响。三十年代出版工作的主流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⑤
1982年10月28日, 经文化部批准(此时出版局已并入文化部) , 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宋任穷,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史良到会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和出版界老前辈胡愈之、叶圣陶发来贺信。会议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陈翰伯主持, 王震、邓力群、许德珩、史良、周扬、朱穆之、胡绳、钱俊瑞、王惠德、周巍峙、吴亮平、高士其等在讲话中, 严厉批判了“四人帮”制造的“三十年代黑店论” , 高度评价了三联书店在党的领导下传播革命理论和革命文艺的巨大作用。应当说,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三联老同志等六百多人参加的这个盛会, 是一个重要标志, 这就是以这次会议及其影响为标志, 完成了对生活、读书、新知以及由其合并成立的三联书店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对恢复和发扬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店成员革命工龄问题的正确解决
在这里, 我未提完成了在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其实就三联书店及其前身的三家书店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出版单位这个问题来讲也已明确了, 但对于参加三店是否即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及革命工龄如何计算问题, 直到1983年5月26日中组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 才得以解决。
关于三联书店从业人员革命工龄问题, 据我现在回忆, 至迟在1979 年就提出来了。从王匡到陈翰伯这两届国家出版局领导班子对三联书店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都是高度重视的, 对三店成员的革命工龄问题多次强调, 要抓紧工作, 以求妥善解决。国家出版局党组还决定由我主持一个小组负责处理包括三联书店革命工龄等落实政策问题。1982年“五合一”我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后又继续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国家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有关部门和同志对此事做了许多调研、协调和争取工作, 并向中组部呈送报告争取早日解决。但我又感到这又是一个难以单独解决的问题。因为粉碎“四人帮”后, 从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开始进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历史上各类与革命运动有关组织的定性及其成员革命工龄问题, 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成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除了一些重大案件由中央个案处理外, 许多涉及革命组织定性以及解决革命工龄问题, 需要由中组部统筹处理。三联书店革命工龄问题就在其中。从中组部1983年5月发出的文件所涉范围之广、组织之多, 即可看出此点。从提出到解决这个问题三年多的时间里, 有三联老同志曾对我和有关同志有所责难,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我敢说不是我们不努力, 是这类问题众多需要统筹使然。
在解决三联书店人员革命工龄问题的进程中, 有以下几点, 需要在这里写出来:
一是徐伯昕、张仲实、胡绳、黄洛峰、钱俊瑞、华应申、邵公文等七位三联老同志于1980年7月20日为争取解决三联书店职工革命工龄问题给宋任穷同志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报告首先谈到:“关于原三联书店职工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革命工龄的计算问题, 各地各部门的处理办法很不一致, 据我们所知, 虽然有认为参加三联书店工作就是参加革命的, 但也有认为原三联书店职工到全国解放起才算是参加革命的。鉴于我们是原三店的负责人, 不少同志要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 希望这个问题得到统一解决。”
报告汇报了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及三联的历史情况, 党对三店及三联直接领导的情况和1949年7月18日党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三店及三联在国统区出书情况及其所起的作用, 最后提出妥善解决的建议:“一、抗日战争前参加三联书店工作的, 一律从1937年8月即三店在武汉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时起计算革命工龄;二、在上述时间以后参加工作的, 从进店之日起计算革命工龄;三、在三店用其他书店、文具店等名义设立的分支机构参加工作的, 以及被派往其他合营机构工作的职工, 也一律按参加之日起计算革命工龄。”
中组部1983年5月26日34号文件基本上采纳了上述建议。
二是在新闻出版总署机要文书档案中查到1983年文化部出版局半月活动纪事中有一条记载:“3月15日宋木文同志和政治处一名干部到中宣部干部局(笔者注:应是中组部老干部局)向郑伯克同志汇报三联书店职工参加革命工作的工龄问题。”
此时已到了解决三联书店职工革命工龄的关键时刻。据说与三联书店相似或比三联书店影响还小的一些组织的革命工龄问题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了。这时, 我和陆圭章同志(曾在中组部工作过)到中组部主管革命工龄这类问题的老干部局再做一次争取。说来也很幸运, 热情接待我们听取我们汇报的这位中组部部务委员、中组部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同志早年在上海做地下党的工作, 对三联书店的情况颇为熟悉, 对我们的要求作了热情支持的表态。据我后来了解, 郑老1909年出生, 1928年在成都参加革命,1933年奉命化名司徒敏到上海做地下工作, 曾任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 同胡乔木、周扬等有党的工作关系, 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界人士有过往来, 对生活等三店在白区革命出版工作的成就和作用评价很高。1936年奉命到延安, 并恢复郑伯克原名。我清楚地记得, 郑老看出我们急切的心情, 郑重地表示, 三联书店革命工龄问题很快就能以下达文件的形式加以解决。郑老之子郑成思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和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曾参加我国著作权法的起草, 九届全国人大期间, 他作为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同我一道参加对著作权法的修改。我曾同他谈起他老爸对解决三联书店革命工龄问题的支持, 他后来告诉我老人家还记得此事。最近, 我又请他转达我对这位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革命老人的感谢和敬意。
三是我通过总署人教司李敉力同志请梁子杰(时任人教司干部处长)、何秀珍同志(总署办公厅干部)于2004 年2月25日到中组部查阅1983年中组部《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组通字「83」34号文件)档案中有关三联革命工龄问题的决策情况。
从中组部档案有关资料看出, 根据1983 年5月7日中组部办公会议决定起草并于5月26日发出的组通字[83]34号文件, 关于决定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1949年7月18日给北京、上海、辽宁、湖北、河南等十三省市党委的批示电》, 就是前已引出的明确“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的领导之下的书店”的《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 以及在1982年10月28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王震、邓力群、周扬同志的讲话和邓颖超同志的贺信摘录。下面是作为决定依据的按档案原貌抄下的四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贺信摘录:
王震:
在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里, 这几家书店象几盏明灯出现了。她们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传播周恩来、刘少奇、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言论。她们出版的书刊,给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精神武装。
邓力群:
象我这样一个人走上革命道路, 应该归功于或者首先归功于三家书店, 以及三家书店的编辑人员、出版工作人员。……三家书店出版的刊物, 出版的书籍给了我很大的教益, 使我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使我能够从里头逐步逐步地加强自己爱国的觉悟, 然后走向共产主义。
周扬:
三家书店是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三家出版机关。这三家出版社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这三家出版社中, 徐伯昕同志……徐雪寒同志……黄洛峰同志……这几个老板——我们那时都叫他们老板, 但这个老板与一般老板不同, 有一种政治的关系, 有一种党的关系……这三家出版社为什么能在群众中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她是党直接领导的出版社。这几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
邓颖超:
三家书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在出版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
在这里做一点补充:周扬同志在纪念会上的讲话, 以《做出版工作应注意文化积累和不断更新》为题, 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下集(1230-1234页)。周扬同志关于三联的性质和作用, 除前述档案摘录的, 还有如下一段:“这三家出版社所以能在出版界、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影响,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我党所直接领导的出版机关。当然, 我们还应提到, 同样是党所直接领导的南强书店、湖风书店这样一些出版机关。它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文艺更早。但是三家书店却存在的时间最长, 影响也最大。它们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如。”
以下是《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有关三联书店部分: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联合后的三联书店, 在建国前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其性质与新华书店一样, 其工作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 其经营目的是为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 在扩大革命影响、唤起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凡是三家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 拥护党的主张, 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 , 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1937年8月以前进店的, 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 年8月三家书店受党直接领导时算起.1937 年8月以后进店的, 从进店之日算起。间断革命工作的, 按中组发[1982]11 号文件有关条款确定。
在党中央关怀下中组部发出的这个文件, 得到了全面落实。三店及其后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近2000名职工(“据1987年编印的通讯录大致有1670 人, 其后略有增补”。见陈原1998 年9月所写《“三联”纪实》, 原载于《联谊通讯》64期)中的绝大多数正确地解决了革命工龄问题。这不仅对三联书店而且对整个出版界都是一件大事, 一件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的大事, 一件有广泛影响的拨乱反正的大事。
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
三联书店在新中国成立后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这家于194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在香港合并组成的三联书店, 其总管理处于1949年春迁来北平, 在1953年出版单位调整中, 经出版总署决定将其编辑出版部门同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合并, 实际上成为人民社的副牌社。
对这个决定不仅有三联老同志心存疑虑,甚至引起胡乔木同志的关注。据陈原同志回忆,1954年上半年(或者1953年年底)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 乔木同志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俗语说“宁为鸡口, 毋为牛后” , 三联书店这块招牌当作纯粹的附属品,那样做使得编者作者译者心里都不痛快, 不如设立一个小小的机构。有些书稿不好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 当然也可以用三联名义, 但三联编辑部总要有自己的方针, 自己的计划, 才能调动著译者和编辑的积极性。这样, 经乔木同志提议, 从这一年起, 在人民出版社恢复建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 由该社副总编辑陈原兼任编辑部主任。陈原同志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从此三联“有点半独立的样子” , 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这个编辑部又停止了活动。
一个出版单位的命运, 也常常同国家的大气候相联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在国家的大形势下, 出版领域经历并完成了拨乱反正, 随着“三十年代黑店论”的批判, 三联书店革命历史地位的恢复, 三联职工革命工龄问题的解决, 关于三联书店独立建制问题也相应地提了出来, 并得以顺利地解决。
1982 年12月8日, 人民出版社向文化部出版局报送《关于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报告》, 并附送人民出版社临时党委通过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方针任务》。《报告》说:“三联书店过去在出版工作方面曾经起过长期的重要的作用, 至今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不久前纪念三联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 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士都勉励‘三联’要发扬优良传统, 作出新的贡献。”在新的形势下, “三联书店亟宜改变多年来属于人民出版社副牌的性质, 积极创造条件, 向独立的出版机构发展”。1983年4月2日, 文化部党组批准了出版局1983年2月19日关于在人民出版社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及其方针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三联书店过去在出版工作方面曾经长期地起过重要作用, 至今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无论从当前和长远来看, 三联书店在向广大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和干部提供文化知识读物, 丰富文化积累以及适应国际国内统战工作的需要, 都应承担更多的任务, 发挥更大的作用。”随后, 经文化部批准, 出版局调整了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班子, 加强了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工作。
1983年11月23日, 胡绳、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周巍峙、沈粹缜六位三联老同志给文化部党组并中央宣传部写报告, 建议将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划出, 恢复其为直属文化部的独立建制的出版社。
1984年2月20日, 文化部出版局为此事写报告给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朱穆之和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周巍峙同志:“遵照您的意见, 我们对胡绳等六同志为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致文化部党组并中宣部的信进行了研究。去年年初, 我们已经在人民出版社内部成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 并准备创造条件,发展为独立的出版机构。故来信的建议, 我们原则上赞成。所谓创造条件, 主要是干部(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房屋两大问题需先解决。我们当积极为此努力, 但目前确实困难甚大。希望得到部里支持, 争取加快步伐。”
穆之同志于2月22日即将出版局的这个报告转报邓力群同志。中宣部于3 月19日复函文化部党组:“穆之同志2 月22 日送力群同志的文化部出版局关于三联书店发展为独立的出版机构的请示报告已收阅。我们原则上同意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 成立独立的出版社, 作为文化部的下属机构。何时开始正式成立, 请你们酌定。”
对出版局领导班子来说, 关于三联书店独立建制的问题早就有所酝酿并持积极态度, 现在主要是解决落实问题, 特别是要处理好“人民”与“三联”分家以及三联独立后的若干具体问题。为办好此事, 出版局决定成立一个筹备小组。考虑到陈原同志在三联书店的威望和对恢复三联书店历史地位所作贡献, 出版局请陈原同志担任由九人组成的筹备小组组长。刘杲同志(时任出版局副局长)以副组长名义参加, 以便于进行指导和协调。筹备小组的工作顺利结束后, 又按陈原同志的提议, 成立带有实体性的三联书店筹备处, 由范用、许觉民领导, 处理三联独立的具体工作。在出版局领导班子中, 仍由刘杲同志继续分管此事。1985年5月28日文化部批复三联书店筹备处的请示报告, 原三联书店编辑部由人民出版社分出, 恢复独立建制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随后又批准在上海建立三联书店。这样, 在京、沪和香港就各有一家三联书店 , 虽有历史渊源,又曾有总店与分店名称之别, 却各自独立经营。
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二十年来, 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扬老三联的优良传统, 图书与期刊出版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 深受广大知识界的喜爱和欢迎。近日, 为写此文, 我翻阅了公开出版和内部保存的三联书店的出版史料, 包括二十年前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的有关文件资料。在这些文件资料中,关于三联书店在新形势下既要继承、发扬老三联的优良传统, 又要在出版体制上有所改革和创新;关于京、沪、港三联如何开展合作, 优势互补, 兼顾国内外读者, 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以及三家按中外合资模式统一经营一个公司, 把出版工作推向海外去, 我认为对今天研究三联书店的改革与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完稿于2004 年10 月2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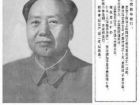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