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马寅初传》
摘要:当时,参与批判的人和批判的具体组织工作也主要是靠了经济系的力量,学校只不过是出面罢了。既然如此,如今平反纠错,自然需要经济系来承担。但是,由于当年批判马寅初的规模特大,涉及面极广,尤其是不少参与者后来在学校系里掌握了权,所以,在北大为马寅初平反不能不遇到很大的阻力。
1978年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中,经济系还要配合学校为马寅初先生平反。马寅初原是北大校长,又是经济学教授。当初批判马寅初,主要是批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当时,参与批判的人和批判的具体组织工作也主要是靠了经济系的力量,学校只不过是出面罢了。既然如此,如今平反纠错,自然需要经济系来承担。但是,由于当年批判马寅初的规模特大,涉及面极广,尤其是不少参与者后来在学校系里掌握了权,所以,在北大为马寅初平反不能不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有人靠批判马寅初提高干部、发表文章、提高职称等。现在,校内外要求为马寅初平反,国内外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评价越来越高,北大不可能顶着不表态。
本来对于批判马寅初的旧事,我并不太在意,因为批判马寅初时,康生来北大坐镇,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布置发动的。当时全国大宣传毛的“人多是好事”。后来得知,毛195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同赫鲁晓夫顶牛(毛被赫要求“对全表”激怒!)。随后中苏关系破裂,全党全国开展“批修运动”并准备打世界大战,声称6亿人口死一半仍然是大国等等。按毛主席的思想,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资源和实力。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心领神会,鼓吹人多力量大,人口越多越好,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理论自然就同毛的主张针锋相对了。康生在北大利用马寅初人口论,在理论界发动了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但偏偏遇上马寅初这样一个“死硬分子”,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样,北大1959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就成了一场很难打的硬仗。批马寅初初期,马寅初很虚心地听取师生们的批判,在经济系的一次批判会上,他带着助听器走到每一位发言者前面,像小学生一样细心倾听他们的发言。但当他把那些发言认真分析后,对自己的人口论更自信了。于是大声地高呼:“我的人口理论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他毅然写出了《我的声明》,抗拒批判,从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围攻,直到最后撤销北大校长职务,取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打入冷宫长达20年。
对北大一般人来说,参加过批判马寅初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当年,北大是8000多张大字报批马,从校园贴到马校长住的燕南园63号,何等气势啊!在那种环境和气氛中,能有几人保持清醒和清白,那时谁能怀疑康生不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谁能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会有战略失误?后来,有一种出自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之口的似是而非的论调颇为流行:“只要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过去错批是对的,现在纠正也是对的。”的确,批也罢,改也罢,都不是群众意志,而是领导决定。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群众,只不过是被运动的工具而已!后来大家都明白了: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既然如此,跟着走的群众是无罪的,是不承担责任的。在纠正冤假错案中,一般上当受骗的群众和盲目执行错误路线的干部是很容易被谅解的。但有的人是整人运动中的获益者,他们不愿吐出从中得到的实际利益,进而充当了新条件下拨乱反正的拌脚石。在北大不少知识分子干部中,这种矛盾表现并不像社会上一般人那样简单和露骨,但矛盾同样是尖锐的。
既然为马寅初平反是不可推脱的任务,也是人心所向,尽管总支书记不积极,副书记作为我就应该当仁不让。于是,我自告奋勇带头编写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协助我的是资料室副主任朱正直同志。除我俩外,萧灼基也曾试图撰写重评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
为了编写为马寅初平反文章,在周琳党委支持下,我和朱直正查阅了大批资料,包括大量档案资料,还多次对马老家属进行访问。这样,我们对老校长的思想更了解,对马老人的人格品德更敬佩了。我们写的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师表马寅初》,由于集中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加上真切的分析评价,文章很有说服力。那篇文章在《晋阳学刊上》发表后,在校内外很快传开了。由于北大无人写这种的文章,我们的论文就代表北大了。后来,此文还载入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人物选编,浙大纪念马寅初诞辰时也印发了我们的文章。
为马寅初平反在校外和国外人口组织引起了强烈反响。报刊上还有人呼吁为马寅初拍传记影片。我们从马夫人和马老的儿子马本寅那里得知,北京“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先生也正在写《马寅初传》,并决定由上海出版社出版。支持邓先生为马寅初作传的是马老的第一位夫人的女儿。这样,北大和北京出版社都被将军了,我和朱正直被逼上了梁山:罢手不写传记,外面压力大,对马老和马的北京家属也不好交待;要写传记又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一本像样的传记,至少也得20多万字,可不是一篇万把字的文章啊!
在这件事上,我和朱正直非常一致,都敬爱马老,愿意通过自己努力把马老的事迹留给后人,也意识到作为北大经济系教师,应当尽这份责任。但是我们都有自知之明,我们对这种文体是外行,缺乏起码的文学功底和文采,很难成功。我们的优势是北大人,掌握着大量档案资料,由北大人根据北大资料写北大的老校长,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于是,我们决心硬着头皮上阵。这期间,还得到了北京出版社的热情鼓励。北京出版社社长左景元同志原是北大的学生,是朱正直的同班同学。左景元得知我们研究马寅初,欣然同意将《马寅初传》列入1984年北京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且表示能保证尽快出书。这样,我就和朱正直干起来了。我们反复编提钢,查资料,并准备约一位中文系的同志合作。为此,我将写作计划报告了那年新来的党委书记项子明同志,约请他为我们的《马寅初传》作序(由我代起草,他修改定稿)。项当时欣然同意。但过了几个月,突然变卦了,说北大校内对马老有不同议论,他不能为《马寅初传》作序言了。过了不久,他就调离北大了。
得不到领导支持,不仅经费无着落,时间无保证,而且要冒风险,根本无法写作。但是在北大也无人敢公开反对我们为马寅初作传。我们还是可以干。
第二年,北大来了韩天实当党委书记。韩住朗润园11公寓,我住10公寓。我听说韩天实原是北大学生,1935年还参加过“12.9”学运,20世纪50年代初,因是高岗分子(原是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被发配到云南,在云南一个工厂呆了几十年,后来上调省委任副书记,又被选派来北京治理北大。韩天实来北大后第一次在办公楼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说:“我来北大是冒很大风险的,来北京后,老朋友们劝我,说北大是是非之地,不可去,但我还是来了。”听了他的讲话,我天真地认为韩天实受过迫害,又勇敢地来北大,可能会支持我们写《马寅初传》,于是利用早晨从朗润园到未名湖散步的机会向他汇报了为马平反和正要写《马寅初传》的情况,并约请他作为党委书记为《马寅初传》作序,还是说等初稿打印好后,我将初稿和代写的序言草稿一起送给他,由他修改定稿签字。他高兴地表示同意了,并连声说:“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此后,由韩天实批准从学校的科研经费中拨给了我们800元做为专项研究经费。有了这800元,我和朱正直更起劲了,钱虽少,但收集资料,初稿打印都够用了,最重要的是它表示领导支持。这时,中文系的合作者又不干了,只能由我们俩人继续干。
由于校外有竞争者,要求出马寅初传记的呼声很高,我们也具备了出版条件,所以信心百倍地赶写。在此期间,我们还经常得到马老的儿女——马本寅、马仰惠的支持和鼓励,并多次参加了马老的纪念活动,于是更不能后退了。
1984 年底第一份打印稿终于出来了。这时,马仰惠的丈夫徐莘先生表示愿加盟我们的书,我和朱正直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决定由两位作者改为三位作者。
徐莘是马寅初的学生,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读商学院,同马仰惠结婚后任马老的秘书。
徐莘解放前曾在杭州中央信托局任会计。1949年夏天,我在杭州时就听说我们商业厅财务处里有一位马寅初的女婿。当时徐莘并不知道我,我却见过他,西装革履一副留用人员的打扮,那时他30多岁,还是很神气的。现在他已是60多岁的老头子了,但提起当年在杭州的人和事,还很亲切。对他的加盟,我们表示热情欢迎。他明白我们的动机是为了写好这本书,大家都不在乎个人的小名小利。
徐先生主动提出承担《马寅初传》中幼年童年部分的改写,我和朱当然高兴。我们的初稿这部分最弱,也最棘手,没有资料来源,我和朱正直也很难想象那时的人和事。徐是老人,他在马家几十年,写起来方便得多。徐还答应为这本书提供马老各时期的照片。这也是很大的支持。关于署名,我提出让他为首,他年龄最大,我们三人论资排辈依次为徐、杨、朱。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说他不是北大人,又是在书稿基本完成后加入的,不能贪天之功,一定要把名字放在最后,说只要有他的名字,就对得起老人了。他的话很中肯,最后我们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三作者的名字排列为:杨、徐、朱。
书稿基本完成后,我为韩天实书记起草了序言稿,按原来约定,专门去十一公寓二门楼上送给他,但这时他又打退堂鼓了,说北大的问题太复杂,他不能为马寅初传记作序了,以免引出是非麻烦。我不明白这是非麻烦是关于传主的,还是关于作者的,反正又吹了。我当时的感觉是,他可能已自身难保,又要被赶出北大校园了。我不等他解释,也不想了解其中的内幕和背景,表示谅解他的难处,就告辞了。后来徐先生请许德衍先生为我们的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
初稿完成后,先打印了20份,供进一步修改用。我们把打印稿,分送给经济系几位对马老特别友好的老先生修改,最帮忙的是赵搏先生和严仁庚先生。严先生在浙大时曾任马老的秘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赵老是马老的多年好友。他们在打印稿上认真作了修改补充。随后,我们又打印了第二稿,送交北京出版社。1986年,一本很像样的《马寅初传》终于诞生了,好难啊!
《马寅初传》出版后,校外反映强烈,书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但北大校内却冷冷清清。北大图书馆和经济系阅览室都没有购书,只收下了我们的赠书。1982年马老逝世后,马老的秘书、东语系教授陈玉龙曾多次建议在校园内立马寅初像,都未获通过。现在,马寅初半身铜像矗立在北大东门逸夫2楼经济学院门前。如今北大校园里外国名人中国名人的雕像一座座矗立着,最高的是勺园对面的赛万提斯铜像,手提长剑,像古代骑士一样神气。不知为什么,惟独容不下三进三出北大的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传》一售而空,出版社说如再出版,只要有6000册定数就可开印,但北大领导不愿订购这本书,北大图书馆也不打算保留这本书。北大领导人赠送外来参观者,多是珍本的线装古书,同现实关系密切的人物传记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没有,更何况在全校大批过的马寅初!对我来说,能将那些事实写出留下公诸于众,也就很满足了。我的小儿子赵萌的媳妇刘天舒1989年以北京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1992年毕业后,赴丹麦商学院攻读硕士。去年,我同她谈起马寅初当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她竟然不知道马寅初曾是北大校长,真叫人难以置信。她却不以为然地说,她的同班同学们谁也不知道,学校和系领导从未介绍过这些校史方面的情况!可见,我们这本《马寅初传》还是很有价值的。
去年,浙江电视台放映了根据几本《马寅初传》拍的《马寅初》影片,青年们终于从银幕上看到马寅初的形象了。马老在学问和道德两方面都是青年的榜样,不愧为一代师表!马寅初校长一再告诫北大人:要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我希望北大的年轻学子们,能记住这位老校长的遗言,时刻准备着接受社会和历史的考验,迎接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
(本文选自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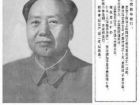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