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出台:不为人知的内情
摘要:《证券法》之所以这么“风风雨雨”,与我国法律起草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大部分法律由国务院起草;还有一部分法律由人大的具体工作小组起草(如《宪法》);另外一部分法律是发动专家学者来起草,《证券法》就是这种方式的首次尝试。
本文为《风风雨雨证券法》一书第六章内容。该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部分成员与华夏证券研究所共同撰写。本文作者张志雄为资深财经记者,现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探讨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如何改进立法过程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衔接,以及如何充分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里有一个立法程序问题”
《证券法》之所以这么“风风雨雨”,与我国法律起草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大部分法律由国务院起草;还有一部分法律由人大的具体工作小组起草(如《宪法》);另外一部分法律是发动专家学者来起草,《证券法》就是这种方式的首次尝试。
在这儿,我们没必要抽象地论述这三种起草方式的利弊得失,如由国务院的具体管理部门起草的法律,虽然更适合“阶段性”或具体现实的要求,却很容易仅仅成为一部“管理法”,对本部门缺乏有效的制约。就事论事,《证券法》起草小组刚成立,就面临着与另一种起草方式——由人大法工委组织起草的《公司法》——的冲突问题。
据有关人士回忆,《公司法》的起草过程也是很复杂。最初是工商局牵头在搞,后来法制局又搞了很长时间。本来打算搞两个法——有限责任公司法和股份有限公司法。最后由法工委来起草,正好与当时的《证券法》起草齐头并进。
如果两种起草方式按各自的轨迹运行,也许还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按人大的立法程序,由财经委专家学者起草的《证券法》转给了法工委去修改。
两种起草方式的冲突之所以成为《证券法》出台的第一个坎,是假定若《证券法》和《公司法》均由法工委起草和修改,这两部法倒“自成逻辑”,很像一套姐妹法或者说是上下篇──尽管正如财经委起草小组所认为的那样,这种“逻辑”很成问题。
1994年3月底,法工委拿出的《证券法》修改稿子,从结构上取消了原来财经委起草《证券法》中投资“基金”、“发行”、“证券监管机构”三章,将原“发行”一章中的“承销”部分放在“证券公司”一章,将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放到了总则中。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取消了“发行”这一章。因为在法工委起草小组的观点看来,“发行”与“交易”是证券市场的两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取消了“发行”这一章,《证券法》就变成了《证券交易法》。人大法工委的同志也不是不明白这一证券市场的常识,只是他们认为“发行”一章已由《公司法》交待,《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仅限于市场交易这一块即可。
不过,要做到这点,《证券法》中的“证券”这一范畴也只能限于股票和公司债券,因为《公司法》中也只规范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投资基金”也就必然被调整掉了(当然,“投资基金”被取消还有其他的原因,但这里所提及的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
惟其如此,法工委方面才在“证券”的调整范围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
除了《证券法》变成了“证券交易法”是个大问题外,财经委的同志还认为有一个原则问题,它涉及《证券法》的地位。因为依财经委的看法,《证券法》和《公司法》是平行的法,它是规范证券市场的一个法,虽然跟《公司法》有关系,而法工委的稿子却有将《证券法》从属于《公司法》之意,财经委的同志当然无法接受。
时过境迁,我们听到的是当初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双方相同的反思。财经委一位同志认为:“这里有一个立法程序问题。政府部门和人大有什么责任,人大内部各部门如何协调,法工委在哪些方面有权改动,改动的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没有规范。”而法工委的同志则认识到:“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探讨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如何改进立法过程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衔接,以及如何充分交流意见和信息。”
顾后还是瞻前
上述的问题若展开来叙述,极有故事性和戏剧性。但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还有更大的难题延宕着《证券法》的出台,显示了《证券法》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发展乃至整个经济体制融合有多么困难。
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立法思路。
从理论上或者从立法的完美性而言,一部法律最好是阶段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但知易行难,更何况是面对“新生事物”的中国《证券法》。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证券法》开始起草的1992、1993年的中国证券市场环境。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虽初具规模,但中国证监会刚刚成立,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正理顺则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上市公司从十几家突然开始膨胀起来,“绩优”、“绩差”根本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至于“琼民源”或“红光事件”是绝大多数投资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券商已有几家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内部机制潜藏着很多麻烦。各省市也纷纷在建立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当然也谈不上今天的合并之类的问题;投资者的人数倒是在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着,但他们在直至六七年后的今天还似乎不断地需要“成熟”。
前瞻证券市场,风险与发展并存,它在考验着当年的《证券法》起草者与修改者的想像力。在这一点上,财经委员会起草小组与法工委小组的立法思路有明显不同之处。前者似乎更着重前瞻性,后者似乎更注重阶段性。财经委小组的基本态度是,既然证券市场和证券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有一般的规律。制定《证券法》应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中的法规体系,即使我们市场中有些市场机制、结构、品种未成熟甚至没有出现,也应该多多包容,给发展留下较大的余地。
比如,对证券品种的划分就不能仅限于“股票”和“公司债券”,还有“投资基金”、“可转换债券”甚至某些金融衍生工具。若仅限于两类,以后出现一类就要单独立法,岂不叠床架屋。现在还不如把大的证券品种规定好,其他以后用部门法规和条例的办法来补充它即可。又比如,关于“信用交易”,财经委的同志认为,“信用交易”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必然的产物。所谓“信用交易”,就是资金的流通与实物的流通可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一致。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就是信用交易。在证券交易领域内同样会有这种需求,若将它卡死,股票的流动性就差了。当然,信用交易有风险,容易出问题,但这是加强管理的事。
法工委的指导思想则是,千万不能立一个法,为消极的或可能违法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哪怕不作规定,等出了问题,再临时作规定管理,也不能把这种事情写到法里。否则,这个法就允许做坏事。因此,他们始终认为,现在没把握的先不写,要充分考虑,不能简单地写。在任何国家,政策法律都有一个连续性的问题,不可能与历史完全脱离开,不受现行体制的制约。理想的东西也许在若干年以后会实现,但在现有的条件下往往很难生存。
在这种立法思路下,法工委与财经委同志对一些问题看法就不同。例如长期争论的《证券法》的调整范围,除了《公司法》与《证券法》的衔接问题外,法工委的同志认为,“争论的实质是我们要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到位的问题”;“我们与国外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他们的证券市场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内部生长起来的。起初这些国家都是放任不管,等出现了问题以后,才开始管理。而我们的市场是政府创造的,政府具有完完全全的控制力。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在立法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比如“投资基金”,在1993年、1994年的时候,虽然有几只基金,但和现在搞的投资基金不同,它们当时都以实业投资为主,证券投资所占比例很小,10%都不到。另外,投资基金是一种信托投资,调整信托关系的实体法应该存在。如果调整基本关系的法律都不存在,谁会来买你呢?就像没有《公司法》,甚至连规范意见都没有,就发行股票,这种股票谁敢买?
对待信用交易,法工委的同志认为,从发展的眼光看,信用交易迟早要搞,但现在能不能搞还必须慎重考虑。信用交易很容易导致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容易引起经济中的“泡沫”,这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大事,因此必须考虑。美国1929年大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1993年、1994年时,我国证券市场普遍存在信用交易,但资金来源是违规流入的银行资金和挪用客户保证金,这就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总之,法工委的同志坚持逐步到位的原则,只往前走,不往后退,看上去慢,实则快。
不过,法工委也不是事事“亦步亦趋”,例如对待券商的经营角色问题,他们就有自己的看法。曾认为券商一律不让做自营,只让做经纪。不管从过去还是现在看,证券市场的人士一定认为这太过分。财经委的同志就认为,证券公司到底要不要做自营是它自己决定的事情。国外也有公司专营经纪业务,但它们是自己要把精力集中在经纪工作,把它做好做精做专,主动放弃自营业务。以往中国证券公司损害客户利益,是怪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营与经纪业务分账的原则。这涉及管理问题,与能否自营是两个概念。
不过,法工委摆出的理由至少也看出了中国市场现阶段的一些问题。他们认为,在股市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国家设立的机构。老百姓参与股市的人数不少,但左右不了市场。要让市场对普通老百姓有吸引力,关键是管住国家的机构。机构赚得太多,个人赔得太多,就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因此,要吸引投资者,必须先让利。券商有资金和信息的优势,如果再允许他们既搞代理又搞自营,利润就很高。这就有一个培植市场先培植谁的问题——是让券商与券商来博弈,还是主要吸引老百姓入市,让老百姓来投资。
当然,最后的市场发展表明,券商的综合与经纪分类管理原则比较合适。法工委同志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从券商的自身发展考虑。我们必须搞大券商,实现规模效益,这样才能与国外的券商抗衡。而我国目前的券商数量太多,规模又太小,为了生存,必然引起恶性竞争,不利于券商的发展。
另外,即使法工委的立法思路如此谨慎小心,也很难预料市场的发展进程。对待“场外交易”,法工委与财经委起草小组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始终赞同搞场外交易。他们认为目前我国有一大批非上市公司,他们发行股票不能转让,转让流通就会造成很大问题,当地政府也很难拿出办法。法工委的同志建议建立一个纯报价系统,为各地店头市场交易提供参考,以防欺诈客户。否则,就会引发一个问题,按《公司法》规定,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必须摘牌,那么这些ST股票今后如何流通呢?
当然,对待是否要建立比深沪交易所层次低一些的交易所和交易中心,法工委与财经委的看法可能还有些不同。对于交易中心,法工委一开始就不同意。因为他们以为,交易中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就是为了争第三家交易所。此外,省里建立这样一个交易市场,是为了让资金在本省范围内流动,否则就流向其他地区了。所以,法工委认为在法中不写“交易中心”,不肯定或否定它,任其自生自灭。
接受我们访谈的参与《证券法》起草工作人士,无论对《证券法》有多少种不同的观点,有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都认为《证券法》的出台应该感谢中国证券市场多年的实践。如果不是这种实践,很多问题只能是束之高阁,可能永远要争论下去。
中国股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必然带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特色──“摸着石头过河”。总结这句话的邓小平同志又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想而知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思路与一般经济发展方针的“设计”在理念上、概念上有多大的不同。平心而论,财经委起草小组的《证券法》方案明显带有一般意义上的“设计”色彩。而法工委小组似乎却是贯穿着摸到多少石头,涉水走了一段路,然后把这类经验升华到抽象的法理的思路。而且,他们经常是对这还很不放心,有几块石头太滑,过是过去了,仍是形迹可疑,暂且放过。再走一段路,看看它们是不是过河必经之路,必踩之石。
[page]走走停停中的政治智慧
我们曾说过,当年刚刚兴起的证券市场在考验着这些参与《证券法》的学者和专家的想像力。其实,这也在测试着政治家的智慧,即《证券法》何时出台以及以何种立法思路与内容出台。
而面对如此变幻莫测的股市,也要求政治家们以现实的态度看待它的作用,或者说,它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
从今天来看,《证券法》七八年的风风雨雨,也是证券市场经历过的,甚至可能有过之无不及。《证券法》起草前,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其中提到了股市,但是内容涉及的是“关门”“不关门”。可想而知,股市在很多人眼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数”,小平同志提出来,则别有深意。其后,虽然几乎所有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人都参观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但他们可能也是将它视为与南浦大桥一般的改革开放的象征去肯定的(当然也包括一定的考察)。1993年股市又成为与房地产一样的泡沫经济的代表接受整顿。1995年,中国股市终于脱掉了“试点”的帽子,彻底关门的“危险”才过去了。接着,政府又需要在筹资渠道与投机危及金融稳定之间的利害关系中作出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终于对资本市场和股份制作出了较为热烈的肯定,但不久以后的亚洲金融风波又让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负面冲击力不能不有所警惕。
《证券法》的进程,似与这种政治家对股市的接受程度与证券市场的功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多少的演进相应合──我们相信,这不是巧合。
1992年7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将《证券交易法》改为《证券法》。1993年8月25日至9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召开,审议了《证券法(草案)》。同年10月份,起草小组对《证券法》进一步修改,此时《公司法》即将出台。1993年12月20日至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召开,厉以宁教授向常委会作了有关证券法起草工作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公司法》审议通过。这次会议之后,《证券法》起草工作由财经委员会转给了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对该稿进行了四次修改后,在1994年初,与财经委等部门在雅宝路北京空军招待所召开《证券法》研讨会。代表们面对法工委起草的《证券法》修改四稿和财经委提出的证券法修改稿,出现严重分歧。
1994年6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召开,审议了财经委、法律委、法工委三个部门共同修改的《证券法(草案)》(有人认为后来正式通过的《证券法》就是在这个《证券法(草案)》的基础上修改形成的)。同时,财经委《证券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至此便告一段落。据法工委同志回忆,本来准备提交讨论通过《证券法》,“但当时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当年的重大问题,就把这件事搁下了”。其间,财经委也一直给委员长打报告、提意见,还是坚持他们原来的看法。1995年8月,王汉斌同志又向当时的朱基副总理汇报了有关的争议问题。之后,中央又向证券委、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征求了意见。其间,法工委又继续修改证券法,并形成了新的一稿(法工委的同志认为现在通过的《证券法》与该稿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人认为与其他修改稿相比,该稿是一大退步,因为“发行”这章被删掉了)。同年12月,李鹏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他指出,人大提出的草案可操作性不强,应继续总结经验,其他部门还有不同意见。
至此,《证券法》几乎走完了我国的立法程序,按法工委同志的总结就是,“提案单位的职责是在提案之前,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也可以先写出一个稿子,让大家来改,改的过程就是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认识提高的过程。等草案提交委员们审议之后,再由专门的工作小组来修改。”但仍缺失一个关键的过程:“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可以先让高层来决策,指明一个方向,从而提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稿子。”很明显,之所以缺失,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言:“这个市场现在还看不清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要暴露一段时间。”
1996年至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期间,《证券法》的立法工作走走停停,务务虚,调调研。
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抓紧制定《证券法》、规范证券市场的精神,《证券法》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其后,法工委与证监会等部门紧密配合。1998年李鹏委员长全力推动《证券法》的出台工作,亲赴深圳市场调研。年底,《证券法》终于出台。
从1992年7月至1998年12月31日,《证券法》的立法之路走得很漫长。但没有政府的启动,肯定还要走得更长。
结语
事情就这么简单。最后像亚历山大面对千缠百结的绳索,一剑砍去,解开了。
当然,为《证券法》费尽心血的专家学者及各方面人士的争论也将载入史册。这里凝聚着智慧,凝聚着对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猜想与反思。正如起草美国《宪法》的那些先贤们的争论,二百年之后,仍有历史学家和后来人从他们的思想中得到灵感。
正如一开始就提到,对这些争论最好的态度是“存而不论”,因为距历史还是太近。近看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可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言,若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中,这些偶然性可能会显现出它的合理性。
也许这些历史的真实与阶段性的结论(当然,包括已出台的《证券法》),最好还是留给后人去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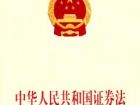

 官方微信扫一扫
官方微信扫一扫